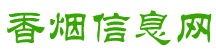|
周末的下午,一个人独自走上龟城的山坡,一缕缕新绿从路边奔跑出来。下山的时候,我看见一户人家门口的桃花已经开的热闹。一绺绺炊烟突然映入眼帘,挟着一阵淡淡的馨香,把我带回老家的屋顶。 炊烟是故乡最丰富的表情,随便一次腾挪扭动,都让我牵肠挂肚,把我带回故乡。从小,每当冬夜,不等鸡叫过三遍,母亲就一骨碌爬起点亮小煤油灯,烧火做饭,背着一个竹子背囊出去了。菜刀何时派上用场,炊烟何时起身,其实很久我都毫不知情,偶尔一次闹肚子,后半夜醒来就不见母亲的人影。常常菜也切了,炕也烧了,饭也熟了,灶火里的火苗已接近收尾的时候,我才迷迷糊糊起床。那一道道炊烟重新爬出屋顶,氤氲出一片温暖,慢慢掏出一案油盐酱醋,掏出一天世俗的日子。于是我常常看见炊烟如细软的姑娘一样舞动着腰身飘向屋顶。 然而,故乡的炊烟愈来愈少了。寻你,有时如隔着一个世纪的距离,你匆匆地蹒跚在岁月的棱角,那是一种永远无法释怀而久远的情结,牢牢纠缠住游子漂泊的灵魂。
父亲,袖着双手从自留地里回来就说,今冬的墒情差很,老太爷又不美美下一场雪,继续旱下去,麦就没命咧,一切就完咧!是啊,旱腰带上的人辈辈靠天吃饭。那时候,看一家日子过的殷实不私自造烟的村子,不用看锅里有没有动静,往往看一眼房顶上有没有炊烟就可分晓。炊烟是温饱的晴雨表,是幸福的一种象征。 自留地就在村子的中央,硷头经常撂着一把撅头或铁锨。父亲迷恋那份土地如中了魔咒,一生都活在一份神秘的咒语里。地西头就是一座小小的庙宇,可是父亲从未进去过,更没有烧过香,拜过佛。父亲相信汗水里能打捞出那个叫做幸福的月亮。相信这片土地就是神坛圣土,这里面就埋藏着一生的福祉,只要无悔的劳作,迟早会刨出一个金疙瘩。相信土地就是佛祖,可是越来越老的果园,价钱越卖越低的现实,让他一天足以抽完仅剩的半斤旱烟。 记得我八岁那年,麦子出穗时,我去自留地里小便,看见一沓毛票散乱地扔在地里,我就回家给父母说,地里长钱了,地里长钱了……虽然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看见这片地里长出过一张钱,但父亲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栽下的果树却营生了我们家到现在。几经风雨变换,斗转星移。父亲终于在年前挖掉了那些他看着如宝贝蛋蛋苹果树。因为那已经是一片不堪入目的光景了。剩下些许树桩,也挂不了几个果子 却如刀子一样天天戳弄父亲的心。星光碜人的寒夜,父亲会一个人看着麦子或者果树到夜半。村庄里随便一声狗叫可以把人从梦乡劫出来,但父亲有时没有母亲的呐喊,那绝对如唐朝的石人石马一样瓷在那里。仿佛那里是家,那里是根,那里是他一生撂不下的牵绊。几声鸡叫声,几家屋顶窜出一缕缕带着火星子的炊烟,路上有走的咚咚作响的村人。一阵突突巨响的手扶拖拉机出村了。父亲有时候才如一个打了败仗的将军一样逡巡着回家。路边的霜又多了几层,他耳旁的白发又增加了几丝。
缕缕炊烟里,母亲喊着我的乳名,喊着父亲吃饭,我常常脚板蹬天,在梦中忽儿地惊醒,爬起来后狼吞虎咽一碗热饭,揣上馒头就跑向北山上的学校。炊烟就紧跟在身后,蛇一样伏绕在我的脊背,追赶着金色的岁月。此时,推着独轮车的老人,担着粪桶的邻居,抽着烟卷的大汉,牛羊的叫唤……一阵嘈杂的声音硬是把缕缕炊烟扯的干干净净。连土地氤氲出的那份绿野仙踪也绽放着活泛的阳光。背粮食袋的人开始麻利地从村里财东人的卡车上用长木板遛下一袋袋麦子,然后扛回去摞起来,长城一样把炊烟荡的远远的。父亲有时也会那样干一阵子,但喝上几口滚烫的开水,砸吧着一卷旱烟,沉醉于故乡抽出的缕缕炊烟勾勒出的想象里。父亲却惦着那片土地,那片果园…… 我常常爬在屋顶,或者挂在树梢,偷看一眼一眼炊烟的模样,那些炊烟精灵一样时有时无,时远时近,如烟如梦,亦真亦幻……蝉蜕一样裹在屋顶,风一吹动,常常让人误以为村上某某过世出了殃,从那户人家屋里钻出来的可怕的殃,神奇而恐怖。死人的事情,犹如吃饭多了睡着了一样。听说出殃的人都是恶鬼变的,做了好多坏事。那是迷信的说法,但也是炊烟里的一份神秘。 炊烟里陈放着一种古老的歌谣,那是怎样一种忘情,怎样一种至乐,忽地在梦一样的光阴客车里走远。那曾经骑着唐朝石马纵横四海的少年不复存在,一颗童心也永远埋在炊烟走失的地平线。只有母亲那亲切的呼唤,还时时回响耳旁,那是游子渴望的声音,那是母亲唤归的声音,那样迷离而富磁性,那样悠长而温暖,炊烟一样,时时萦绕着人世的每一条没有希望的路,也陪伴着生命每一次微笑的时刻。吃一碗粘面就蒜,喝一口凉水,咥一口锅盔,都是炊烟的味道,都是故乡的毒药一样直入骨髓。
后来,去山上邻村上初中,一次次钻在千丝万缕的炊烟里呼朋唤伴,西家跑,东家窜,天不明,我们就连颠带跑的奔赴命运的战场。穷孩子大都是靠读书改变命运,我读了许多书,走过许多人没走的弯路。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考上了高中。 后来我去县城念书,有时候一个月才回家一次。每次回家,远远看见炊烟从村子上空升腾,心里就分外的温馨,而肠胃此时就咕咕的叫唤着。而黄昏时分,故乡的炊烟则随着晚风飘的老远老远。那是浪漫的星斗,那是情人的眼睛,窸窸窣窣的暗处,谁又演绎这乡村一段温暖的故事呢?炊烟是一份乡愁。 村南边,孤独的小瓦屋里,没有娶上媳妇的王姓青年吹起了竹笛,时常把一些幽怨声音扯上天空,和炊烟一样抛洒的老远。那是一次命运的远足,那是青春的一次阵痛。千年的石人动了,将军催动着千万大军,时常临于窗前。冷月无声,呼呼啦啦的铠甲声里,谁是英雄,谁是美人,笛声呜咽如长河之浪,低吟迷离如愁云横空,一缕缕炊烟心慌不安,个个溜出屋顶倾听一个关中汉子的寂寞豪情。英雄迟暮,石马依旧,谁的笛声吹破大唐旧梦?谁的故事掐断炊烟万千?
从小,每一次离家,母亲半夜里就起身,爬在被烟火薰得发亮的灶门口,一把一把送着柴禾,翻动着火苗。灰烬里是母亲那颗熠熠生爱的心和被岁月夺去的朱颜。每一次离家,母亲绝对不会让我空着肚子上路 ,给我烙千层饼,兜里塞上两个鸡蛋,一双亲手缝制的棉鞋……而母亲常常把锅灰弄的满头满脸都是,即使头发丝乱作如茅草一片,母亲却顾不得理会。母亲一生都在锅灶四周来回转,尽了一个传统的中国妇女应尽的一切义务。 炊烟里,我常常忘记母亲,忘记故乡的炊烟呛人的味道。常常全家的泪水和母亲的泪水是被烟火薰出来的。每逢天阴下雨,炊烟就窝在灶房里不出去,或者大风天气,或者柴禾发潮的时候,每一顿饭都是母亲用眼泪薰出来的。那一顿饭里包含着多少心酸和忧伤,也隐藏着多少贫穷和无奈……父亲常常也扯着喉咙数说着什么。也被炊烟撂的老远。 每一次回家,我都如候鸟一样飞渡枝头,一个梦来不及好好做醒,却要离开,心里空荡荡的,没了底。于是,每一次回家都怯火起来,回家母亲总要问西问东,问我在单位过的咋个向,和妻子处的咋样,女儿的学习如何……凡是她能想到的都一个个问,我经常无以回答,就匆忙如炊烟一样扭身离开故乡。
每次收拾好一些带的东西,毕了,母亲都眼睁睁看着我离开,想说什么却也什么没说出的样子。作为一个儿子,我却常常做不到耐下性子倾听一个母亲的絮絮叨叨的声音,我心里也是纠结,如那片永远萦绕心头的炊烟一样,永远飘荡在村庄的上空。 离开故乡,再回望故乡时,那一缕缕炊烟里总能扯出故乡的一大堆人,一大堆事来……一切又是让人万分揪心和难耐。 是的,在现代社会私自造烟的村子,人类的故乡慢慢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被不断破坏,被遗忘……可我们永远都是被故乡抛弃的游子,当你生活在灯红酒绿的都市,当你醉身万丈红尘,当你寄身水泥森林,当你跨越千山万水……你何曾记得 身后永远有一条牵扯着衷肠初心的炊烟,你何曾觅得那些遥远的记忆?炊烟永远定居人类的记忆深处,那是一份温暖感。 故乡的炊烟伴随着我又一次出发。从我离开的那刻,寸步不离,袅袅起身,伴着我走进我如陀螺一样旋转着生活的小县城。于是,我常常抽身变成一缕温柔的炊烟,爬向城市的天空。城市的高楼大厦一夜多了无数,乡村的土地几天少了大片,我将飘向何方,我辈尚有故乡,而不远的明天,我的灵魂漂泊向哪里呢?炊烟愈来愈少,人情温暖愈来愈淡,唯有飘在故乡上空的炊烟,生命部落永恒的图腾高挂人类史册的扉页。
一缕缕炊烟晕染着思念深重的故乡,一声鸟鸣吐出村庄里的树林,暮色四合,母亲在并不遥远的乡下此时缝补着什么,我猜不是缝补着一份沉甸甸的思念,就缝补着故乡的天空。炊烟是故乡永不消失的风景。有炊烟的地方就是人类的故乡。故乡永远是游子思念的码头,而炊烟就是那一条永远联系着你离开的缆绳。你无论走向何方,炊烟都是你最轻盈而久长的行李。 炊烟是一缕乡愁。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无声无息地舔舐和抚慰着人类的灵魂,有人类的地方就有炊烟的踪迹,炊烟袅袅升起的地方是每一个人的故乡。没有炊烟的乡村,是寂寞和空虚的,万千繁华也是镜花水月一样轻渺。浮沉人生,大河奔涌,炊烟是乡村的灵魂,是永恒的乡愁,也是人类灵魂最美的皈依方式,也是人类生命最后的歌唱。
乡土中国 之 美 乡愁、远方、梦想 『关注啸鹤艺术精彩无限』 专业引领乡土中国文化 时刻温润精神心灵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