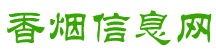|
前年初夏回国修整旧屋,拆墙时候见到嵌在窗子上面一条不起眼的横木,俗称过木。父亲不经意地说这根木头已有百年历史,它是当年地主四轮马车的车辕,我心中不禁感叹村庄历史就这样被保存在村中的秘密角落。不忍青史尽成灰,于是收集国史、方志与家谱,书写这个无名的小村。 小村平畴沃野,宜于农桑,前为公路,后为良田,东邻河流,西与山东鸡犬相闻。村中住有六十余户,两百多人,这在烟火万家的淮北平原上实在是小村。小村虽小,但名气并不小,方圆十里无人不晓,特别是中老年人。这是因为小村的大地主。 学界对于中国北方村落的研究,多倾向于将乡村精英置于国家与乡村的维系与调和之中,即杜赞奇所谓的权力文化网络。小村的历史表明村庄地主的权力是内植于乡村内部,并非源自国家授权或城乡网络。小村地主以圩寨为基础,进行自卫,从事农业生产,维系乡村运行。小村地主村社组织的衰落源自抗战之后国家政权的强行介入,最终官僚机器取代地主成为乡村主导者,开始各种乡村试验。 乡村街道 黄河小村 小时候,总以为黄河很远,可是黄河却在小村经流六百余年,今日村中依约可寻黄河当年的印记。例如村人常用河堤的沙土,晒干过筛之后作为儿童和老人的尿布,细软的黄河沙土是绝佳的尿不湿。村中某些地名也依稀可见黄河的影子,如村北有处叫大(Dai)王庙的田地,而大王庙实为当年敬奉黄河之神的庙宇。 丰县处于江苏省西北角,为汉高祖刘邦的故里。刘邦征伐天下后,衣锦回乡,将出生地恩封汤沐邑,轻徭薄赋,这是丰县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丰县的衰落归于黄河,南宋时期黄河开始改道南流,丰县从此江河日下。明代万历间潘季驯筑两岸大堤,使黄河全流夺淮,经今开封,商丘,徐州至江苏入海。 黄河以含沙量大著称,明清两代奉行“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河患,但也使黄河成为地上悬河,成为两岸生民头上的一把利剑。丰县不幸正当黄河之冲,黄河流经丰县南境,数次决口漫漶,城郭倾圮,庐舍荡然。明嘉靖五年(1526),黄河决口将丰县城陷于水中,县治被迫迁移。十九世纪以来,束水攻沙的治水方略已经走到尽头。黄河平均两年即漫决一次,甚至一年数决。咸丰元年 (1851) 八月 ,黄河又在丰县决口,冲出一条大河(俗称大沙河),全河走丰县,苏北鲁南汪洋一片,被灾严重。 黄河决口洪水的威力超常人想象。据乡贤记载,黄水所到之处,村庄一阵尘烟高起,房屋立刻化为乌有。水退之后,楼下一层全部淤于泥中。明代丰县城已在地下数十米,可见丰县黄河沙土淤积之深厚。2014年,丰县南部河道清淤,发现一艘清代嘉庆时期的木制商船,已经深埋黄土之下,让人感叹沧海桑田之变。 明清两朝的黄河洪灾以及王朝连年的河工耗尽了流域内的资源,黄河两岸已经山穷水尽。1855年黄河改道之后,守着残山剩水的黄河故道立即成为王朝的弃地。根据哈佛大学政治系裴宜理教授的研究,黄河泛滥导致淮北地区人无恒产,很少有人能积累超越别人的财富,黄河讽刺性地在这层意义上起到了均贫富的作用。1855年黄河取道山东入海,才给小村及周边地区休养生息的机会。至19世纪下半期,本地的地主开始有了更多的财富积累和剩余,开垦荒地,营建村落,从而也成就了今日我居住的小村。
远眺初夏的小村 乡村老屋 便集地主 小村最早叫茅庙,因为有座茅姓的家庙。村庄先是被渠姓买下,后又被村南三里便集的刘姓地主买下建寨。便集原名荆冢村,相传荆轲之冢所在。荆轲刺秦未成,随被秦王剁为肉醢,盛装于瓮罈之中,分埋于全国三十六处,警示全国,泗水郡的埋葬选址即今便集村,故名。丰县博物馆所藏北宋碑刻就载有荆冢村。明朝隆庆年间,便集已是丰县西北著名的大集。依照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便集是茅庄所在地区的中心地。 刘氏自洪武年间迁居便集,绵延数百年,有古丰刘氏之称。刘氏聚居便集北部,土地遍及周边地区。咸丰辛酉年(1861),刘姓大地主的季子移居茅庄,以便管理耕种便集北部的田地,这种村庄,地方俗称为外庄子,茅庄即是便集地主的外庄子。刘氏选定此村,因为村子紧邻河流,八方归水,是一块上风上水的宝地,而且距离老庄便集只有三里之地,可以相互呼应。 1861年,刘姓地主移居茅庄之时,正是捻军在淮北蜂拥而起之际。咸丰六年(1856),捻军染指丰县。咸丰八年(1858),捻军围攻丰县,纵兵屠城,二千余人遇难,史称戊午兵事。自此之后,丰县乡村民绅为保全身家性命,先后捐资修筑寨圩45座,其中39座修筑于咸丰十年(1860)和咸丰十一年(1861)两年间。在这种背景下,移居茅庄的刘氏地主开始营建茅庄,将其打造成为一座地主庄园。 小村庄园 近代淮北兵匪横行,在淮北乡村,对农民生活影响最大的设施无疑是圩寨。根据民国吴寿彭的调查,淮北的圩寨中心有一家高大的瓦房,另再有一个炮楼,作为寨主的宫殿。寨主是有一百顷二百顷或者更多的数目的田地,四围有数十百家的农民,大都是种着寨主的土地。茅庄就是这样的地主庄园。 茅庄与鲁西南一路之隔。鲁西南民风强悍,素有豪强与土匪的传统,村人称之为山东大麻子。他们专门拉户,即绑架人质,索要赎金,因此当地村落基本都有看青会及红枪会等民间武装组织。地主的寨子更是这种防御性社会生态的集中体现。
刘氏经营茅庄,以刘汝舟为代表人物,刘汝舟为移居茅庄的第二代地主。其人处世精明,为人练达,购置地产,有田三千亩,同时继续营建茅庄,将其最终打造成为一座北方乡村的地主庄园。大院、寨墙、炮楼、海子和牌坊成为村落布局的主要元素。 村庄居中为刘家大院,占地几十亩,房屋上百间,一律青灰色的砖瓦房。在瓦房建筑群体中,错落有几座砖木结构的二层楼,俗称堂楼。牛马厩在地主大院前方,酒坊在屋后,村子西北角则为打谷场。周边则是佃农的茅草房子和土墙院落,环绕而居。 村子四周筑有高高的围墙,南面有一座坐北朝南的大门楼以供出入。寨墙四角均有一座炮楼,留有枪眼,以供瞭望防守。寨墙之外是一丈宽的壕沟,沟中有水,村人称为海子。今日痕迹犹存,是村中主要的排水格局。此外,地主还有十几杆汉阳造的枪和几门土炮,以习武之人作为团练,守卫村庄。 村外东南不远处还有一座牌坊,是刘汝舟为养母杨孺人而建的节烈牌坊。牌坊为纯石结构,有立柱四根,高约四米,上书对联曰:“擗踊在灵前,之死已存靡他志;从容随地下,此生不作未亡人”。立柱南北各有卧坐狮兽八只。我少年嬉戏时候,曾见其中一对石狮,弃于乱石之间,其雕工之精致绝非平民之物。牌坊上有横梁两层,长约二丈,前后雕镂龙凤,四角各缀有铜铃,清风徐来,声闻数里。 庄园是个完整的生产单位,还有酒坊酿酒,酒坊专门雇佣酒大工,即酿酒师,选用本地高粱,常年驻庄酿造高粱酒,其酒据说质地纯净,芳香浓郁,非今日勾兑酒水所能比肩。酒坊之酒不仅供应地主自用私自造烟的村子,而且还在邻村流通,小有名气,祖父当年曾尝过此酒。有一年我从台湾带回金门高粱酒,祖父品尝之后,连称有当年地主高粱酒的味道。 地主因家大业大,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因此专门雇有乡村厨子烧饭。厨子平日精研改良地方菜系,形成十里八村特有的毛庄菜系。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无论酿酒还是菜系,只有地主有财力与时间传承和发展所谓的地方文化,如同中世纪欧洲乡间的贵族一样,他们才是乡间传统的守护者。 清末以来,群雄逐鹿,草木皆兵。刘汝舟不惜财力营建圩寨,不仅保护了自己的家族与财富,也为地方村民提供庇护,所以丰县县令曾送他保卫桑梓的匾额。现在茅庄六十余户居民中有十五个姓,深刻地反映了村中的移民性质。村民多源自当时苏鲁两省的农民。例如我家祖上为鲁西南单县的张家,五世祖张宾为明朝成化乙未科进士(1475),官至南京光禄寺卿,单城东门里有张家高大门楼。张宾之后,家道中落,族人多以务农为主。民国中期,曾祖父兄弟四人移居茅庄,成为地主的佃户。 烽火故园 茅庄地主庄园的衰落始于抗日战争。抗战之后,进可攻退可守的茅庄庄园因处于苏鲁边界,成为日军,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角力的地方。强权之下,地主的乡村体制开始崩溃,而裹挟在政治洪流之中的小村地主,从此很难全身而退。 1938年5月,日军占领丰县县城。国民政府退守丰县西北乡村,由国民党丰县常备队队长黄体润组织抗日力量,设有八个大队。其中,总部和一半兵力驻扎在茅庄周围三里之内。1938年底,中共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一千五百多人,用苏鲁豫支队番号,开进丰县周边地区,首战歼灭丰县日伪军八百多人。自此,国共开始在丰西地区合作抗日,而苏鲁豫支队驻扎茅庄。1939年元旦,黄体润曾住在茅庄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部。1939年底,黄体润曾拟定在茅庄宴请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以及李贞乾,郭影秋等,后因移防而作罢。 1940年6月,国共交恶。国民党江苏省第五区行政专员汤敬驻扎茅庄,与中共发生冲突。国民党战败被赶去本区,而中共在距离茅庄十里的张后屯村建立丰县政权,从此小村周边形成中共政权,国民政府以及日伪政权三足鼎立的局面,相互攻守。无论共军,国军还是日军,都超出小村地主的掌控。 战火纷飞,故园零落。刘汝舟其时已经病逝,三个儿子带领全家避难徐州城,而这只是流亡的开始。抗战之后,为了巩固根据地,中共开始开展土改。便集老庄的地主作为典型,被拉到村东桥头,就地枪毙。刚刚回乡的茅庄地主,在惶恐之中再次踏上逃亡之路,再次避乱徐州城,而这次却是不归之路。 消失的牌坊 1949年,避难徐州的刘树猷和刘树森被新政权逮捕,关押在丰县监狱。三地主刘树品因为年轻,涉世未深,被发配回村。1951年“镇反”期间,在监狱关押二年的刘氏兄弟,被三地主用车推回村中公审,随即枪毙于邻村。三地主因年轻,免于一劫,被判劳改二年,之后又重新回到村中劳动,寄居在生产队的牛棚之中。 新的政权通过革命运动深入乡村,清除地主构建的乡村组织和传统,取代地主成为乡村主导者,进而开始共产主义的试验。卓尔不群的小村在同质化的革命运作之中,泯然众人矣。土地被分配给本村以及附近的农民。庄园的房舍,寨墙和炮楼全被拆除,砖石被村民拉走建房。为了寻找宝藏,地主大院更是被掘地三尺,硬生生挖出一个大坑,可惜一无所获。地主的酒坊,因为长期酿酒,层积了厚厚的酒糟,是上好的农家肥。大跃进时期农业积肥,村民将酒坊的酒糟挖尽,从而形成另一个深坑。 “文革”之前,村中地主的痕迹只剩牌坊和三地主本人了。牌坊仍矗立于村子东南方向,不觉换了人间。父亲读小学时候还常常路过,在此乘凉。1966年,拉倒牌坊的日子终究到来了,两位村民在百余名红卫兵鼓动下爬上牌坊,用绳子拴在牌头,用了两天时间将牌坊拉倒并捣碎,围观者千人。丰县地处黄河故道平原私自造烟的村子,缺少石料,因此牌坊的石头很快被村民疯抢,铺路修桥,建设房屋,还有部分用作砌猪圈或改为猪石槽。牌坊的石兽被生产队当作拴牛马之用,百年之物,从此泯灭。 牌坊倒掉之后,三地主不断被审问家中的财产下落,他只得交代出一处位于马厩石槽旁的藏钱地点,红卫兵随即挖出了几麻袋铜钱以及两块银元宝。初战告捷的红卫兵,再次批斗三地主,要求招供以前家中枪支的下落。自知在劫难逃的三地主,于头一天晚上在牛棚中上吊身亡。第二天被发现后,一席裹尸,埋在村东河堤。 牌坊构件 地主的传说 1966年之后,地主在村中已是庐墓无存。对村民而言,地主的意义只剩下银元了。“文革”期间,生产队在一次挖土积肥的时候,在地主当年的茅房中挖出三千块银元,这也见当年地主的财力。村里决定私分,全村三百人,每人分得十块大洋。可是不久走漏风声,乡里闻知,每家被要求将银元上缴乡里信用社,换取氨水化肥。祖父当时家中九口人,分得九十块大洋,由父亲背着前往乡里上缴。正读初中的父亲急需钱财,于是私自留下一块,谎称路上丢失,竟然得以过关。他用这一块大洋兑换了两块六毛钱,买了一支当时稀有的钢笔以及作业本,还有一双玻璃丝的袜子。“文革”后期,住在地主老宅基地附近的一对兄弟,哥哥在刨树时发现一罐银元,藏在家中,秘不示人,打算私吞,可是家中幼子童言无忌将其说出,引得兄弟反目。
村中最为传奇的是地主家中的一口水缸。1950年代在村寨的南门附近,一辆生产队载重马车的车轮突然陷落,坑口是一口倒扣的大铁锅,而被压碎的铁锅下面竟是一口青花瓷缸。有人认出这正是地主家的水缸。缸中装满了绸缎被面及女人衣物,但是挖出不久,绸缎衣物见风就变成了灰烬,只留下这口大缸。此缸为圆口,直径约一米,高约八十公分,白底印有蓝色菊花。缸身为双层,中为真空,类似于今日暖水瓶,具有保鲜作用。 这口青花瓷缸被生产队作牛棚储水之用,每晚用于淘洗草料,水可以几日不腐。逢年过节,则被生产队食堂作储糖之用。可几日不坏,令人称奇。七十年代末,生产队解散,所有公物拍卖。此缸要价30元。当时祖父是生产队长,父亲在卫生院上班,经济比农民稍好。在祖父劝说下,父亲买下这口缸。当时父亲一个月工资5元,30元是他半年的工资。 幼年时候,记得此缸放在家中堂屋的西间,盛放面粉,即使炎炎夏日,面粉从来不生虫。九十年代初,此缸以1200元的价格被古董商买走,当时父亲月工资200元,这还是他半年的工资。 村老传说地主还有一口印有金色老虎的大缸,但是至今尚未出土,所以地主的传说仍在继续,因为财富。怀璧其罪,此言不虚。 参考资料: Elizabeth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刘文忠:《人争一口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东方杂志》第27卷第6号,第71页。 丰县档案馆藏:《黄体润日记》 丰县便集《刘氏族谱》 单县张集三官庙《张氏族谱》 个人采访,2015年6月,首羡镇茅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