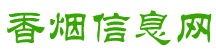|
那个年代,交通还不发达,通信行业也不如现在兴起。由于村子里活计不多,很多男人都选择去外地打工,养活家里。从那时候起,不仅多了留守儿童,也多了很多留守妇女。一年上头见不到几回,男人偶尔从外面打电话回家,还得去村委会去接。就像牛郎织女一般,一年团聚一回。这种情况多了,两方互相牵挂,有的是心理上的,有的是生理上的,但是也甚少有逾矩的。——题记 在安明镇的一处乡村里私自造烟的村子,到了农忙的时候,能把人累得直不累得直不起腰来。平时农闲的时候呢,又能无聊出花儿来,毕竟那个年代也没什么娱乐活动,无聊倒在路边看蚂蚁搬家的大有人在。今晚轻雾漫捻那一缕淡淡的忧伤,成一帘凄美的幽梦。寂寞,于是开始无边无际,漫天漫地微微颤抖于夜的凉风中。 已经是入夜时分,初夏的晚上还有些凉爽。云婶儿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开始思念远在城里打工的云叔了。已经好几个月没见了,云婶儿很挂念他,想念的都有些燥热难耐了。到后头竟然有些心烦意乱,埋怨起木叔来了,一去这么久不回来,把她一个人留在这村子里。到后头,实在是睡不着,心中仿佛有火在烧。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来,去外面院子里打了一桶井水上来,痛饮一大碗。这个天气,井水还是很凉的,也之后这凉飕飕的井水能慢慢平息心中的火焰。日子一天天过去,已经进入了盛夏,天气越发热了起来,后来的井水也是没什么大用了。 又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云婶儿早早上了床,但是翻来覆去半宿也没睡意,索性穿上衣服走到了院中。好像快十五了吧,月亮真圆,如圆盘。云婶儿拢了下衣服,倚在磨盘旁看着满是星星的夜空,不由想到,也不知道老云是不是也在看这轮圆月和星空呢?要是老云能陪她一起看就好了。想到这里,云婶儿不由得笑出来。暗笑自己的不矜持,害羞的仿佛脸都红了。皎洁的月光映照在她的脸上,让她更加娇艳。也不知怎的,云婶儿又觉得有些口渴发热,连忙跑到井边提了一桶水上来,准备重新去洗个澡。
已经到了深夜,几乎没有哪家人还没入睡了。除了蝉鸣蛙叫声,也就是邻居家的狗子偶尔叫唤几声。在这个夜里,云婶儿烧好了水,关上灯,趁着月色泡进了浴桶里,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打在云婶儿身上,肌肤娇嫩如少女,她用手掬起一捧水从肩头浇下,水珠在后背流连,让人浮想联翩。夜还长着,这个澡还能再洗洗。 慢慢地水已经开始变凉,微凉的水也正好能平复烧得正旺的心火。她撩着凉水涂抹在丰润的肌肤上,让自己的心也随着一起沐浴起来。心头的躁动渐渐被凉水湮灭,云婶不由得叹息一下,苦笑着干脆仰躺在盆中,让水没过自己身体,只留下鼻孔喘息。 云婶才三十出头的年龄,一副任凭风吹日晒也不减其色的瓜子脸,依旧如院内那株盛开的牡丹,娇艳欲滴,又仿苦夏之玉兰,明艳温馨。云婶就是这般的美,只是美丽的眼神中隐隐闪现着不为人道的抑郁。平淡的日子咋就给过得有些水深火热了呢。
临近夏末,万顷青纱帐一下就长起来了,四野如碧海潮生,天地间更加生机勃勃。农家人施完最后一遍肥,玉米地里除了一遍杂草,总算可以短暂地休息一下了。每到这个时候,村头树下、巷尾屋山头阴凉地里,总能遇见三五一群的男女老少,聚在一起侃大山,缺大空。 女人们往往会熟稔地纳着鞋底,细针白线,在充足的日光下,有些闪眼。男人们自然就是烟不离手,吞云吐雾,深吸一口,缓缓打鼻孔滤出来。要是不小心烟到了女人,定会被娇嗔的粉拳擂上两下,贱的男人还挺享受。嘻嘻哈哈的人们倒也不耽误吹牛,上知天文地理,时事八卦,下到东家葫芦西家瓢。直至大到国际风云变幻,总会有人能一番唾沫星子四溅,说得子丑寅卯头头是道。其间当然少不了那些谁谁家男人挣了多少钱,谁家女人,在男人不在家的时候,忽然换了多少件新衣服,吃穿用度变得“阔绰”了,八成是……那些揣着谑意的妄测,总是每次侃大山的重头戏。
之后,人们要么叹息一番,要么一副事不关己的谑浪笑傲,再然后自然是趾高气扬地一通鄙弃,好像自己才是圣人门前那棵松。云婶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员,只是难得见她开口,总是在一边静静地听。到了该笑的时候,才会稍扬唇角,以示配合。 这村子里,做人可不能太疏群了,不然可能就要被孤立了,到时候指不定背后就有一大堆长舌头对你指指戳戳。待到日头稍西斜,气温略略下去一点,人们才嘻嘻哈哈去田里,看看庄稼长势,顺带给自家的青山羊割一些嫩草。农闲间隙也就这样慢慢打发了。 云婶是个闲不住的人,男人不在家,要强的她,除了把地种得有模有样,家里几头青山羊也养得膘肥体壮。每次看着几头羊圆肥滚滚的架势,她心里美滋滋地笑着,要是能保持下去就好了,年底可不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不仅孩子上学的费用有了着落,还可以给老云买上几瓶好酒。
每天傍晚从脚踏三轮车上拿下青草,饲喂那几只宝贝羊,这是云婶每天最快乐的时候。看着羊儿们吃得津津有味,如花般的笑意不时地在她那弯凤眉上跳跃。当然,还有一个羞于启齿的小秘密:夜深人静时,辗转在床上想念木叔。三木叔其貌不扬,面瓜脸,两腮微坠,身体略显胖,矮壮敦实,远远看上去着实像是一个大木瓜,木叔的名字便是村人们因此戏谑得来。 不过他天性憨厚,为人随和,在村里人缘极好。老云小时候家境不好,小学都没毕业。那年月的农村人,基本上很少出门,也无处去学技术,所以他挣钱门路也很少。也就是这两年时间,跟随村里的包工头到青州的建筑工地干点体力活,家里才开始慢慢有了一点点积蓄。他有一身力气,趁着年轻,很想多挣几个钱,让自己的女人和孩子过得舒服一些。 在工地上干了几个月,没学会砌墙,也就只能在塔吊下面装砖打灰了。木叔不吝啬自己的力气,很卖力地干活。为了多挣钱,原本是两个人的活,憨憨厚厚的老云愣是请求包工头给自己一个人做。起早摸黑地干啊,干啊。每天收工以后,拖着酸痛倦怠的躯壳,他必须花上两块钱,给自己买两袋一斤装的板桥酒,然后仿佛铐着脚镣一般,一步一步挪去工地上的小吃摊。再花上三块钱,一块钱买咸水花生豆,一块钱买五个山东老馒头,剩余一块钱,就舍上老脸请求老板多多少少给点青椒炒鸡皮。
一通猛造,一路跌跌撞撞,晕晕乎乎的老云又回到工地,一头扎进自己凌乱不堪的小窝。刚倒下去的瞬间,呼噜声已然骤响。有工友忍不了他的噪声,会半开玩笑地一脚蹬在他屁股上。然而,他太累了,此时此刻,大概就是天塌地陷也难以让他醒过来。 转天,蒙蒙亮,又是生龙活虎的老云,早早又开始了一天的搬砖运动。日复一日,老云也就这样熬下去。每次想起家里的孩子老婆,他疲惫的身子立马又像打了鸡血,什么艰难困苦能击垮一个心有方向,努力为之奋斗的男人呢? 每个季度末的最后一天,是发工资的日子,每到这一天木叔就特别开心。一拿到工资,就马上去报刊亭给家里打电话。电话是打给老家村头小卖部上的,家里没有多余的钱安装一部五百元安装费的固话。 从家到小卖部,不远,可也不算近。每次听电话,衣着合体的云婶都是一溜小跑奔过来,娇喘吁吁,胸前的小兔子颤巍巍地跳动,惹得路边闲磕牙的村人都要偷偷侧目,更有几个小子不怀好意地偷乐:“云婶,慢点跑哦,不要摔倒喽。”“滚!”她总是头也不回地斥骂两句,一群瘪犊子玩意,懒得理你们,脚下却是缓了缓。 等待的这几分钟,老云很兴奋,不停地在报刊亭边搓着手转圈圈,那个就要响在耳边的幸福,让他难以抑制自己狂跳的心。他面前好像已经出现了媳妇那吹弹可破的笑脸。想媳妇喽哇。电话接通后,老云酝酿好的那些体己话就像憋住了一般私自造烟的村子,怎么都说不出口。东扯西扯半天,只能老生常谈。“我今天发钱了,后面有工友回老家,托他给家里捎回去,真舍不得花钱给邮局手续费。” 放下电话,老云抬手赏自己一个嘴巴,嘴笨的东西,咋不知道问问媳妇过得怎么样,孩子好不好。一阵阵懊恼盘旋在木叔心头。他不知道的是:云婶其实更想他。待到青纱帐棵棵上开始出天樱了,短暂的农闲也即将结束,又要开始准备秋忙了。前几天刚下过雨,玉米陇行里杂草又起来了,水灵灵的,尽是些山羊很喜欢吃的青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