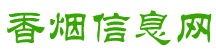|
我是一把有身份有地位的白铜水烟壶。 过去,有资格拥有一把像我这样的白铜水烟壶的人物,不是王公贵族就是军阀大贾,最不及也得是地方上的加V大号,就连慈禧太后都是我的铁杆粉丝。 那个写出《白鹿原》的老陈头是个超级烟民,这不是啥秘密,网络上有他两根手指熟练又潇洒地夹着烟卷的照片。我敢打赌,他也是我的粉丝,肯定拥有不止一把像我这样的水烟壶,有白铜的、黄铜的、竹子的、名贵檀木的、镶嵌着和田玉烟嘴的;而且,他必然也是一个吸水烟的行家里手,要不然,为何在《白鹿原》小说里会有那么多吸水烟的情节描写呢? 听说了张嘉译要把《白鹿原》搬上荧屏的消息后,我非常激动,像我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白铜水烟壶终于能够在全国观众面前大大地露脸了,而且是在这样一部史诗级大剧里。就在《白鹿原》播出的当天,我特意邀请来黄铜水烟壶、竹制水烟壶、檀木水烟壶、镶嵌和田玉烟嘴的水烟壶一同观看,就连我的远房亲戚印度水烟袋也巴巴地赶来捧场。当电视中出现白秉德手拿一杆旱烟锅的猥琐画面时,我的节操瞬间碎了一地。
看看这画风,这哪是史诗级大剧该有的?这分明是《关中刀客》好吧?我甚至能够想象的出,下一刻,白秉德老汉挺身而起,挥舞这杆旱烟锅,一记烟锅拂穴手点中了白稼轩的笑穴,笑死他个不肖子!
我知道,此时此刻旱烟锅一定也在笑,某宝的工作人员想必已经与他接洽,商量“白秉德老汉同款旱烟锅”广告代言的事。在电视剧未播出之前,我已经拍好了“白稼轩同款白铜水烟壶”代言广告,“你在乎你的价格,我追求我的价值,我就是我,有不一样的烟火,我是白铜水烟壶,我为自己代言”,多好的词儿,就这么被张嘉译无情地咔嚓掉了。 我就纳了闷了,你们《白鹿原》剧组找一把像我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白铜水烟壶有那么难吗?张嘉译你告诉我,有那么难吗?是的,在过去,拥有一把白铜水烟壶的人最次也是个加V大号,虽然以前的加V大号不像现在这么普遍,虽然以前的加V大号不能花499元轻松通过认证,但还是有一些的,至少在白鹿原及其周边地区就有白稼轩和郭举人两个。你们也没必要把两把都找来,一把足矣,大家轮着用吗,毕竟同框吸水烟的画面也不是太多,不得不同框时就找个替身吗,不就是多买一份盒饭吗?又不用买工伤保险。 不是我自抬身价,我真是一把有身份有地位的白铜水烟壶,你以为随便一个人就能用我吸水烟?像鹿三那样的长工可用不起,不是因为他身份低下,也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因为他没“闲”。 《白鹿原》原著中写到: 吃罢晚饭,白嘉轩悠然地坐在那把楠木太师椅上,把绵软的黄色火纸搓成纸捻儿,打着火镰,点燃纸捻儿端起白铜水烟壶,捏一撮黄亮黄亮的兰州烟丝装进烟筒,“噗”地一声吹着火纸,一口气吸进去,水烟壶里的水咕嘟咕嘟响起来,又徐徐喷出蓝色的烟雾。他拔下烟筒,"哧"地一声吹进气去,燃过的烟灰就弹到地上粉碎了。 吸水烟一定要突出“悠然”二字,所谓的悠然,就是要闲、就是要慢、就是要静心,媳妇推进产房的当儿是吸不了水烟的。鹿三也吸不了,他白天要上地,从地里回来要喂牲口,喂完牲口要铡草,忙完东家的活要忙自己的活,忙完自己的活还得回屋尽尽人事,实在是没有时间悠悠然的吸水烟,只能蹲在槽头上,趁着牲口吃草的空儿,抽出别在裤腰带上的旱烟锅,从烟袋里狠狠地挖上一锅烟梗沫儿,紧着吧咂两口过过瘾。 所以说旱烟锅是烟草界的下里巴人,水烟壶是阳春白雪,而像我这样的白铜水烟壶,则是水烟壶界的王公贵族。白鹿原上也只有白秉德老汉拥有一把,后来这把白铜水烟壶传给了白稼轩。鹿泰恒没有,他用的是黄铜水烟壶,说白了其实就是简配版,当然还有丐版的竹制水烟壶,据说盘龙镇上的四大富户各有一把,其中白稼轩的岳父吴长贵用的是一把镶嵌着黄铜锅头的高配版。
讲这些我不是想突出阶级,更不是要分出贵贱,只是在陈述事实,只是试图让大家明白,像那种长柄旱烟锅不该是白秉德老汉的标配装备,即使吴长贵也羞于拿在手中。这就好比是笔挺地名牌西装配个运动鞋,娇滴滴的大家闺秀粗口骂街;就好比是商场墙壁上巨幅广告模特像胸部嵌着一块插座板,热气腾腾地羊肉泡馍碗里搁着一只上校鸡块。总而言之三个字:不和谐! 水烟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的印度,当时吸水烟在印度王朝的统治阶级圈子里极其盛行,一度被看做“舞蹈的公主和蛇”,随后逐渐风靡到阿拉伯地区。十六世纪中期,大概是明朝万历年间,伴随着烟草的传入,水烟壶也经由丝绸之路传到中土,当时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一壶一路”。 敬业的波斯商人不仅把烟草和水烟壶带到了中国,还手把手地教给勤劳的中国人如何种植烟草和制作水烟壶。后来,甘肃兰州一带的农民朋友传承了烟草种植技术,江苏苏州的工匠朋友传承了水烟壶制作技术。白稼轩所吸的“黄亮黄亮”的烟丝儿就是正宗兰州黄条水烟丝,用的白铜水烟壶则是江苏著名匠人汪云从亲制。 汪云从什么人?他是清代著名的制壶名家一手烟货源云霄,载入《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的大匠人,那可是树碑立传的人物。白秉德的那把白铜水烟壶设计精湛制作精良,烟管、吸管、盛水斗、烟仓、通针、手托严密紧凑浑然一体。烟仓上盖刻有“汪云从刻制”字样,将盖子压下,不摇不晃严丝合缝,如此高超的工匠手艺而今恐怕再难见到。白秉德的这把白铜水烟壶不仅仅是一把水烟壶,那是一件艺术品,更是其身份和修养的象征。而你,张嘉译,你却把它换成了粗鄙丑陋的长柄旱烟锅,若是白秉德泉下有知一定会气的活过来。 过去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一手烟货源云霄,更没有“今日头条APP”,庄稼人忙活了一天拿什么消遣?很多时候都是一家人围坐在堂屋屋檐下听家里的老人们讲古,老头老太端着水烟壶斯斯文文地坐在中央,下首是老实巴交有些拘谨的儿子,儿媳妇坐的稍远一些摸着黑纳鞋底。待到老人一连抽完三锅水烟,引发一阵歇斯底里的咳嗽,“啪叽”一声吐出一口浓痰来,这才开口讲那些永不重复的故事。最想听故事的永远是小孩子,他们也是爷爷奶奶抽水烟的虔诚学徒。一见爷爷奶奶们拉开了讲故事的架势,赶紧把整个身子偎进老人们的脚湾里,一边就抢着持那点着的纸媒子,只等装好一锅烟,就将纸媒送到嘴边,“噗”的一声吹出明火来,再凑到烟锅上把那金黄的烟丝球儿点燃。抽完一锅,又早早的抢着通针,即使爷爷奶奶将烟丝吹出来了,也要“刷刷”通两下。祖孙配合默契,什么农耕劳作的艰辛、邻里地边的不快统统烟消云散了。 好了,该说的我也说了,不该说的我也说了。张嘉译还有《白鹿原》的编剧们,你们看着办吧,我需要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