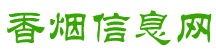|
据史料记载,烟叶原产于南美洲,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在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初的明朝万历年间。主要有两条传入线路:第一条线路经吕宋(菲律宾),传入福建、广东地区,再传至中原地带。第二条线路从日本、朝鲜传入我国东北地区。 烟叶作为主要的经济作物,曾经在天中大地广泛种植。上世纪80-90年代,在西平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烟叶,一是上级下达有种烟任务;二是种烟有一定的经济效益。烟叶生产从育苗栽培、到田间管理,从缉烟装炕、到出炕分拣,再到上交烟站出售,过程非常辛苦,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比较深刻。 老家的烟地在村子东北一块儿叫做“大路东沿”的田里,我曾参与过田间管理“掰烟叉”“打烟叶”。“掰烟叉”就是烟叶在生长的过程中,像树木一样,会长出许多枝丫,为了防止烟叶养分流失,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把烟棵上多余的“烟叉”掰掉。“掰烟叉”要趁早,得迎着露水下地,等到太阳出来温度升高时,烟叉上渗出的烟油会粘在虎口和手掌上,非常不好清洗。后来市场上曾出现一种能阻止烟叉生长的“神药”,只要往烟叉上一抹,就不用再频繁“掰烟叉”了。“打烟叶”就是根据每棵烟“下、中、上”层烟叶成熟时间的不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把先成熟的烟叶摘掉。“打烟叶”与“掰烟叉”一样,浑身上下也会沾满露水和烟油。“打烟叶”要有一定的“眼力”,如果打的烟叶太“生”,将来炕出来的烟会发青,既“样”不上等级,也卖不上价钱。
烟叶打回来以后,下一个工序就是“缉烟叶”,也叫“织烟叶”。“缉烟叶”需要烟杆子和烟荆子,烟杆子通常用竹杆、洋槐木或桐木烘烤去除水分制作而成,通体光滑,重量较轻,结实耐用;烟荆子在“外张”(出山)街上能够买得到,一般整团子(整蛋子)出售。由于每家每户都有很多烟杆子,为了便于区分,烟杆子的两头都写有名字。“缉烟叶”需要两个人配合,负责缉烟的人先用烟荆子在烟杆子的一头打个结,递烟的人以2-3张烟叶为一把,将“烟把儿”对齐后递给缉烟的人,缉烟的人把烟叶往荆子上缠绕两下,再往前一推,一左一右交叉进行,在缉烟叶的过程中,还不时将已缉过的烟叶向前推一推,确保整杆子烟叶厚薄均匀,最后在烟杆子的另一头也绾个结,这样一杆子烟叶就编织完成了。母亲干活儿麻利,缉烟叶的速度快、效率高,往往几个人递烟叶才能跟得上趟儿。 缉完烟叶,接下来就是“装炕”。村子西北角和村西头当街各有两间炕房。炕房墙体为土坯垒砌,地面上挖有炕道,炕道用泥巴掺麦秸制成的盖板封闭。炕房墙体上横穿着10几根檩条,房顶留有两扇天窗,开启闭合靠两根绳子拉动。“装炕”得从上到下装填,身材瘦高的天顺叔、祥甫叔是装炕的能手,只见他们两腿叉开,交替站在高处的两根檩条上,下面依次安排若干个“二传手”,接力的队伍一直延伸到炕房门外,外面的人把织好的烟叶一杆一杆递进来往上传,依次架在檩条上。炕房装满后,用塑料布蒙住炕门,外面再用麦秸帘子压住。烧炕更是技术活儿,烟叶在炕房内要经过“变黄、定色、干筋”三个阶段,炕道温度设置、升温速度、保持时间都需要把握好。党爷、怪爷、立东爷、坤才大伯都是烧炕的“专家”,他们烧炕出的烟叶品相好,能够卖高价钱。经过连续几天的烘烤,终于等到了烟叶出炕的时候,乡亲们都满怀期待,炕门一打开,眼前是一片金黄。出炕的任务都是村里的男青年担任,这时候炕房内的温度还比较高,往往是光着膀子出炕仍汗流夹背。出炕的烟叶经过各家各户仔细辨认,分别装到准备好的架子车上。
刚出炕的烟叶比较焦,容易破碎,不能立即分拣,须放在地上稍微上潮后再整理。记得下雨天是分拣烟叶的好时候,分拣烟叶时要按照国家规定的等级分拣、抻开铺平,同一等级的烟叶扎成小把,放在一起。卖烟叶时,将扎好的烟叶用破床单子或尼龙袋子缝制的“烟包”兜住,放在架子车上或捆在自行车后座上。那时候每个乡镇都有烟叶收购站,根据烟叶“下、中、上”不同的部位,设置了“柠檬黄、橘黄、红棕、杂色、微带青、青黄、末级”等42个不同的级别。虽然各个烟站定的收购价格一样,但是对烟叶等级的把握程度却有差别私自造烟的村子,为了能卖个好价钱,通常卖一次烟,得跑好几个乡镇。听母亲说,有一次她和本家的几个堂嫂舍近求远跑到“酒店”街卖烟,托“熟人”才卖了40多块钱。在那个物质匮乏、经济条件落后的年代,卖烟叶也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烟叶季节过后,烟杆子和烟荆子就会被整理起来等待来年再用。烟杆子捆成捆一般“立”在牲口屋的门后或“棚”在梁上,烟荆子则缠成一个个线蛋子,放在荆条“箩头”里。
各个烟站收购的烟叶在进入烟厂之前,需要在烟叶复烤厂里进一步加工处理。记得在西平县城“西上公路”旁边就有一家烟叶复烤厂,我当时在红旗高中(西平高中)上学时,经常能闻到复烤厂里飘过来的浓厚的烟草味儿。 那个年代,市面上卖的成品卷烟比较“主贵”,“阿诗玛”“红塔山”称得上是当时的顶级好烟,大众化的卷烟品牌也比较多,如漯河卷烟厂的沙河,驻马店卷烟厂的发时达、春雷,西平卷烟厂的双燕、洪河,遂平卷烟厂的汝河桥等。一般情况下,农村人“办事儿”是舍不得买这些成品烟的,大都自制卷烟。我家就有一个木质卷烟器,也叫“烟推子”。记得它是一个长方体的木盒子,中间嵌一水平木块,木盒子左右边框镂空,便于辊子来回移动,木盒子的一端是固定的辊子,用帘布与另外一个活动的辊子连接。制作卷烟时,在帘布凹陷处放入适量喷过白酒的烟丝,用手指压实,推动辊子,在帘布的摩擦力作用下,烟丝被卷成圆柱状,推到水平木块时,放入烟纸,在并在烟纸边缘处抹上浆糊,继续向前推动辊子,卷烟便落入卷烟器另一端的凹槽处,用切刀把多余的烟丝剪掉,一根卷烟就制成了……为了美观和便于存放,自制卷烟会装入用报纸或书纸做成的烟盒内,也叫“白包烟”……想当年“烟推子”是立过大功的,二舅家盖新房子、俺家东屋翻修,就是用“烟推子”制成的白包烟“支迎门事”。
在老家,除了白包烟,平时最流行的卷烟还是“喇叭头”。“喇叭头”制作方便快捷、简单易学。可随手撕一张作业本纸或书纸,靠一侧取适量烟丝或烟沫摊在上面,保持一头大一头小,然后斜着将整个烟纸卷起,用少许“口水”沾湿将卷烟纸粘住,再将“喇叭头”多余的纸叠进去,形成封闭,这样一根“喇叭头”烟就卷成了。当然也有人吸不惯“喇叭头”,偏爱吸长烟袋。记得党爷就有一根长烟袋,一头是铜质的“烟袋锅”,另一头是扁平的“烟嘴”,烟袋杆上吊着一个“烟布袋”。吸烟时将“烟袋锅”在“烟布袋”里挖一挖,再用大拇指摁一摁,用火柴点燃,吸上几口,“烟袋锅”里的烟草一明一暗的。吸完烟,党爷经常把长烟袋别再布腰带上。 提到“喇叭头”,我便会想起本家族的祥叔。他是村里有名的木匠,凡是请他打的“家什”做工精细、引领时尚。由于我长年在外上学的缘故,与祥叔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有一次我经过村子北边的树林,碰到祥叔一个人在剜草,中间休息时,只见他忽的站起身,从耳朵根处取下一根“喇叭头”,点火后猛吸几下,下巴在胸前左蹭右蹭,肩膀还一耸一耸的,一只手指向远方,嘴子念念叨叨“使…,使…”,究竟是啥意思?也许只有他自己清楚。后来我才知道,祥叔是因为婚姻家庭挫折精神上受刺激所致。看着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状态、那种场景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也许只有烟草才能使他“享受”人生,暂时忘记一切……
说起烟叶,不能不说其功效。从医学上讲,烟叶具有行气止痛、驱风散寒、祛瘀消肿的功效;用烟草加生石灰泡水,还可以防治蚜虫、菜青虫等多种害虫。但烟草的危害性也比较大,据了解,烟草中含有大约1200种化合物,毒性最大的是烟碱,又叫尼古丁。一支香烟中的尼古丁含量为6-8毫克,足以毒死一只老鼠;二十支香烟中的尼古丁可以毒死一头牛,50-75毫克尼古丁就能致人死亡。长期吸烟会造成体质下降,诱发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肺癌以及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烟草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大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创建“无烟环境”而努力。 随着国家政策调整和种植结构的变化,目前私自造烟的村子,除了部分地区还在种植优质烤烟外,烟叶已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转眼间30多年过去,老家的几亩地已不再种了,流转给亲戚帮忙打理;昔日的炕房和烧炕人早已化作尘烟;祥叔也已驾鹤西去多年;烟杆子、烟荆子、烟推子也早已荡然无存;当年装炕出炕的“年轻人”亦是儿孙绕膝…… 但烟叶带给我的记忆却永生难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