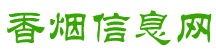|
乡村生长着炊烟,炊烟是乡村的明信片。 庄户人家坐北朝南的老屋,无论是三间还是四间,一进堂屋门不是左边就是右边,都有一个连着炕的锅台。那锅台青砖砌就,白灰抹缝,整齐干净,上面安放着一口八印的大铁锅,绿树掩映的屋顶矗立着烟囱,冒出的乳白色炊烟袅袅升腾,争先恐后飞向蓝天,就像神仙用画笔在蓝天上描画出的祥云,家家户户屋顶上的祥云弥漫开来,就织成了一张薄薄的纱缦,护佑着村庄,成为乡村里最亲切、最壮观的图画。 一日三餐,锅灶为大。只要锅灶不倒,锅里就煮着世世代代的日子,无论春夏秋冬,炊烟都会升起,成为乡村最熟悉、最靓丽的风景,是乡村最清新、最明亮的明信片。 然而,不是所有的时候,炊烟都会青云直上,早晚不同的时光,有风无风不一样的日子,炊烟的模样和姿态,是不一样的。 清晨的鸡鸣,唤醒了酣睡的乡村。因为无风,睡眼惺忪的炊烟从烟囱里一柱涌出,朦朦胧胧,凝结在一起,热气腾腾地直上天空,化作青云,融入苍穹中的晨曦。有风的日子,风吹烟散,丝丝缕缕,荡漾到村外的上空,在旷野的雾霭中,如仙女般潇洒地舞动着衣袖,轻歌曼舞。若是清早,晨风凉爽,空气湿润,炊烟如水,漫溢开来,柔软如锦似纱;到了晚上,村庄宁静,炊烟也跟着沉寂,久久笼罩在村庄的夜空,徘徊成一个迷离的梦幻,风吹着它,变成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在空中盘旋,奋力向上攀登。 袅袅炊烟,为乡土所孕育,是乡村独有的浪漫。
小时候在野外剜菜割草,塘湾洗澡,盐场的荒水池、送水道里钓鱼,到了太阳隐去身影,霞光万道的时候,就会看见村里升起缕缕炊烟。那渐向野空飘去的炊烟中,我能准确无误地认出哪一缕是自家的。透过袅娜的炊烟,我仿佛看见田间劳作归来的娘,洗去脸上和手上的尘土,把饭食放进锅里,盖好锅盖,抱一大捆秸杆作为柴禾放到锅台前,坐在蒲团上燃着了火,拉动着风箱,咕哒咕哒的风箱唱着古老的歌谣,火光在锅膛里跳跃,炊烟由锅膛穿过炕道,奔向烟囱,喷薄而出,直冲霄汉,与晚霞携手并肩,轻盈起舞。微风拂过,炊烟变成了行走的云彩,飘浮在村庄的上空。望着天空的炊烟,我像渴望归巢的小鸟,心里情不自禁地涌起一阵阵回家的冲动。这时,随风飘来的炊烟,送来娘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傍晚的朦胧中,我隐隐约约地看见娘站在村头,手搭凉棚朝我这边张望,便三步并做两步向家里奔去。 炊烟是一条亲情的彩带,一头攥在母亲手里,一头系在儿女身上。炊烟将饥肠辘辘的孩子牵回家,不管锅里煮的是苦涩还是甜蜜,再粗粝也能嚼出心满意足,咂巴出称心如意。
炊烟与暮色,仿佛天经地义、天造地设地绘就了一幅温馨的水墨画。黄昏,牧归的牛羊驮着夕阳踏上归途,群鸟结伴飞过鳞次栉比的屋顶,进入归宿的密林,孩童的嬉闹声回荡在街头巷尾。虽然天色已晚,但炊烟却生动无比,就像大地抛向天空的情丝,又像是一首断断续续、缠绵悱恻的情歌。各家各户的炊烟,让天空显得明亮高远,乡村更加寂静幽深。散发着香气的饭菜摆上饭桌,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全家围坐在一起,开始共享粗茶淡饭的时光。月色溶溶,星光点点,洒满了乡村,照耀着一户户美满温馨的庄户人家。于是,老人们说,无论岁月多么艰难,只要有炊烟,就有希望。炊烟升起,锅里就有吃的,就有了生存的命脉,就有了创造美好幸福的勇气与力量。
细细地嗅一嗅炊烟,是木柴曾经繁茂的气息,是青草拥有过的青春芳香,是秸杆上阳光的味道私自造烟的村子,是泥土蒸腾的清香,是村庄那永不消失的乳香。有了炊烟,就有了村庄,望见炊烟,就进近了村庄。没见过炊烟的人,不太懂对家的牵挂。每天私自造烟的村子,庄户人习以为常地在炊烟上挂满家的味道,倔强地把炊烟定格成家的方向,一天天、一年年,炊烟被雕琢成心灵的归宿,剪不断,理还乱,许多人甚至一辈子没有走出炊烟划出的半径。 民以食为天,这是人类生存的不二法则。 要烧熟一日三餐,烧旺日子,就离不开添柴加火。为了使锅灶里孵化出炊烟,打柴拾草列入庄户日程。于是,为锅灶准备烧的,成了孩子们放学后或节假日,必不可少的功课。父母清晨上工前和傍晚收工后,甚至是在田间劳作的罅隙,都捡柴剜草。天寒地冻的清晨,男人身穿棉裤棉袄,腰扎草绳,撅起草篓,扛上铁笆,到村外沟坡河滩鎗拾冻草。人们清楚,谁懈怠了炊烟,换来的只能是清锅冷灶。
有柴草的日子,锅灶不再冷清,肚肠不再忧愁,漏风透气的老屋便有了温暖,灶火映红的时光里,炊烟理直气壮地融入蓝天。 在那个缺油少面、缺腥少咸的岁月里,炊烟顽强地滋润着庄户日子,养育着那难以忘怀的年代。 春日,娘早早地起来,把铁锅洗刷干净,添上一瓢水,锅底淘上两把小米,锅梁上熥着昨晚煮熟的地瓜和烀好的玉米饼子,盖上锅盖,生火后用力拉动着风箱,往灶膛里填着柴草,风箱咕哒着唱熟了早饭。夏天,娘把我和弟弟从海里钓来的硄鱼和被称作“寨花”的鲈鱼等,以及摸来的白虾,去腹除杂,先把白虾放进锅里清水炸熟私自造烟的村子,再将鱼儿下锅,加上油盐酱醋红烧,悠悠炊烟将鱼虾的鲜冽传遍街巷,海味的浓鲜为平淡的日子增添了些滋味。深秋的乡村,简直就是地瓜的世界,收获回家的地瓜成堆成垄,琳琅满目。娘把一个个红皮大地瓜洗净装进锅里私自造烟的村子,添上水煮起来。灶膛里的火舌舔着锅底,不一会儿就烧开了锅。水蒸汽带着地瓜的香甜随炊烟飘满村子,原来,全村几乎家家都在煮地瓜。地瓜熟透端上饭桌后,有的松软如泥,食如甘饴,有的面若豆粉,咬上一口噎人。冬日,北风呼啸,地冻冰封。只一宿的光景,一场大雪不期而至,早晨起来推开门,满目银装素裹,屋顶也披上了一层厚厚的雪。冬天的庄户人家,尽管缺肉少油,但冬储的大白菜和用豆子到生产队豆腐坊兑换的豆腐还是有的。娘把大白菜和豆腐切进锅里,锅沿上烀上一圈玉米饼子,熥上地瓜和秋天我哥儿俩钓到的晒干的硄鱼,大火烧开,温火清炖,炊烟浓白流畅,从屋顶飘向天际。锅膛一生火,屋里就暖和了,屋顶上的积雪比别的地方融化的都快。在化成的雪水沿着屋檐落下的嘀哒声里,锅膛的火候恰到好处,锅盖揭开,白菜鲜嫩,豆腐飘香,干鱼的鲜味直往鼻子里钻,配上焦黄的饼子,甘甜的地瓜,寒凝大地的严冬里,有着如此丰盛令人垂涎的美食,农家是不难熬过寒冷的冬天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乡村远离了清贫,在庄户人沐风栉雨、爬摸滚打中,日子变得丰润起来,炊烟变得明快欢畅,飘出的缕缕炊烟没有了忧愁和辛酸,而是充满着醇香和甜蜜,农家的生活像炊烟挺拔升高。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开始远离了炊烟的生活。城镇化的浪潮汹涌澎湃,一个个村落在旧村改造中消失,不仅是现代炊具对氤氲炊烟的打压,炊烟喂养大的农家子弟,都看不懂炊烟的表情,读不透炊烟的语言,他们将梦想和希望打进行囊,背叛炊烟走出乡村,越走越远,走到望不见故乡炊烟的地方。炊烟失落了,显得单薄瘦弱,作为乡村的明信片,日渐泛黄模糊。 乡村在时光中日渐苍老,少有的炊烟就像是它稀疏的白发,炊烟呼唤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现代生活的暴风骤雨席卷着乡村,煤气灶淡蓝的火舌焚烧着古老的传统,电饭煲、电炒锅、电磁炉、微波炉、烤箱如一股股洪流,冲毁着乡村的炊事习俗,就连现代都市里,楼房公寓也巧妙地将炊烟隐去。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罩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尽管我喜欢这种宁静与诗意,然而却随着炊烟渐渐散去。这些年,家乡每天都在变化,日子真正像芝麻开花,庄户人家多了幸福,少了叹息,没有了愁苦,住房喜新厌旧,炊具不停更新,田间的秸杆不再是柴草,它们不是饱暖了牛羊的胃肠,就是化作造纸厂的崭新纸张,要不干脆那来那去,土地养育了它们,它们粉身碎骨秸杆还田,融入泥土,化作肥田的养料。还有,如今庄户人也讲环保了,说是炊烟弄得乡村乌烟瘴气,污染天空,因此,每当做饭时,只闻饭菜香,不见炊烟起,家家户户吃不冒烟的饭。尽管村里还有像娘一样对炊烟心存感恩的老人,虔诚地对待炊烟,认为炊烟应像田间的禾稼,年年繁盛,生生不息,忍受着烟熏火燎,顽强地坚守着、培育着那缕缕炊烟,但却显得那么势单力薄微不足道。城镇化的巨浪,终将会把炊烟淹没,乡村的日子正在被现代化的彩笔改写。
我不知道最后一缕炊烟在哪里留恋徘徊,也不知道这缕炊烟何时消失,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将再也看不到炊烟。炊烟这张乡村的明信片正在逐渐看不清,变成一片空白,成为一张废纸。我更知道,没有了炊烟,就没有了乡村,人们就失去了故乡。然而,那一缕缕惜别的炊烟,终会在我记忆的窖藏中酝酿成永不衰老的乡愁,继而站成一道道风景,叠印在我心中的底片上。 又是红霞满天时,我乘坐着风驰电掣的汽车,在两侧是楼房的公路上穿梭。远处,一缕炊烟升起,在落日的余晖里飘荡,仿佛是家乡伸出的手臂,紧紧地拉住我。 我突然明白,炊烟是最朴素、最纯真、最具个性的人间烟火,是离家最近的路,它总是萦绕在我的心头,使我的乡愁绿意葱茏,生机盎然。即使有一天它荡然无存,也会化作无限的憧憬,催生出崭新的希望。 作者简介 刘好军,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青岛市作家协会理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