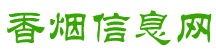|
《丁真的世界》©时差岛 - 世 相 故 事 - 无从考量的还有刘文黄和剩下27口人的去处。通过社交平台,日益渐火的北长滩和北长滩沿线的这条道路—66号公路,让当地政府也嗅到了致富的气息。而如何合理合法又合情地迁走这些留守居户,成为了官员的当务之急。 ”信息时代下,突然闯入的年轻人,用网络打破了一个村庄的宁静。而本该宁静终老的村民,不得不重新面对生活。 -1- 三个着蕾丝裙的姑娘穿过夹着沙砾的马路,朝黄河滩头走来。10月底的黄河,正处于日渐来袭的枯水期,在正午的阳光下,和村庄一起昏睡,看上去有些不合时宜的泥泞。 姑娘们踩着高跟鞋踏过,左右避让,摇晃不已。 这是西北宁夏自治区中卫市下辖的上滩村。和相邻的黄石漩、榆树台、下滩村3个自然村,统称为北长滩。它是黄河进入宁夏北岸的第一个小村庄,被崇山峻岭裹挟在其中。这里也是66岁老人,刘文黄的家。 “这个房子至少一百年以上了。” 这是近两年来,刘文黄对不断探入的新面孔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不是他想说,这句话只是在回答闯入者的提问,满足好奇。的确,没有瓦砾,一层层夯土敷起的黄墙,在周遭残垣的荒凉下,还余下几分萧整。 刘文黄的房子立在村子的最中间,也像这里所有的房子一样,它立在无处不在的沙土中。为了遮挡沙子和阳光,房子前檐搭起封闭的院子,可沙土依旧侵进墙壁,漫上土炕,渗入被褥。 炕上艳丽的被褥,像是在对抗沙土,故意造出一些颜色来。已经变成烟色的木头房梁,上面依稀可见“天长地久、古千秋”的褪色对联。而墙上贴满的识字图片,无声地述说着,这顶屋檐下,还居住着一个刚开始学字的孩子。 廉价塑料的识图是孩子的妈妈添置的,在去年过年的时候,她回来了一趟。“在外头打工,搬石头。” 刘文黄解释道。 3岁半的小姑娘叫五五,五月初五生。还没有开始上学,村里没有幼儿园,更确切地说是没有学校。想要读书,需要去到将近50公里外的城甸。因此,她也成为村里仅剩的28口人中,惟一的小孩。 五五喜欢每天跑到村头去,看闯入村里的外人。奶奶腿脚不算好,甚至跟不上一个三岁小孩的脚步。天真,悲戚,祖孙二人的神情泾渭分明,瘠薄的沙土中,黄墙若隐若现,依稀可见斑驳。 “能给我糖,还有大盒的饼干。” 这是五五跑去村头最为重要的理由。五五说这些糖是一些小姐姐们给她的。 她口中的“小姐姐”一般是指外来的观光客,这些不速之客的终极目的是在朋友圈秀出一系列美图。信息发达的时代,贫瘠落后反而有了更为时尚的定义——“小众、非主流”,这也是她们选择打卡地的至高标准,吸引眼球就代表着流量,而流量则意味着名利。 虽然,这只是她们的臆想认知。
-2- “ 朝那头走,那边有羊,还有牛。” 五五碰见了穿蕾丝裙的三个姑娘,知道她们想要什么,投其所好。 “哎呀,太好了,看来可以出大片了。”其中一个姑娘朝举着相机的同伴笑道。 “谢谢小妹妹,真可爱。” 丝毫不吝啬言语上的夸赞,目之所及,是苍茫的天地,是隐秘而小众的景色,她们举着现代化的产物走来走去,却注意不到脚下始终留存的破败与贫瘠,自然也看不到五五眼里的期盼。 没有得到糖和大盒饼干,五五怂拉个脑袋,朝相反的方向挪去。孩子的忧愁总是转瞬即逝,走出约莫50米远,五五看见黄土地边冒出来的一丛杂花,兴奋之情便再次燃起。 治愈孩子的方式,或许就这么简单。可五五爷爷的症结,就不容易治好了。 “怎么办,搬到哪里去。” 爷爷刘文黄,拿着一杆旱烟枪靠在马路牙子上。 “前几天政府又来人了,给俺家下通牒,这个月25号前,必须都搬走。” “可它那个房子,我们哪有钱,住得进去。” 同在一处的邻居大妈附和道。 大妈口里的房子,是政府棚户区改造集中修建的小楼,在50公里外的中卫市。政府试图接管村子里的土房,把剩余的居民全部迁移到市区,统一规划,打造旅游区。代价是,各户需要每年支付3000-5000元不等的费用。 “一年到头,我也攒不下这么多钱。” 刘文黄的确攒不下这么多钱。他家没有牛,整个村子,只有一家人,拥有这种价值不菲的物种。5只驴,是刘文黄家最大的一笔财富。 “放它们出去,省事儿,到了天冷,自己就回来了。” “舍不得卖,除非没辙了。” 没辙是刘文黄的实话,一年3000左右的收入,是老两口这个家庭全部的经济来源。 “换些生活必需品,平日里的吃食还是够的。土豆、芋头还算好种,再不济树上还有些枣子、丑梨,院子里还能种点沙葱。” “7年前还种点小麦,现在也没地了,都淹着了。” “不过,今年树上的枣子、丑梨也不准俺们打了,全都掉了,只能夜里偷偷去捡一些。” 刘文黄对此有些不满。 在村子里的道路旁,除了倾覆的黄土沙地,也生长着不少果树。即便生长得歪七八扭,但在这样的土地上存活,本身就是一股力量。 “没人管,以前随便吃,后来有了些外来人,就打来卖点。现在有人来看着,不准打了。” “不好卖,一天也卖不了多点出去。3块钱一斤,还嫌贵。” 刘文黄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只晓得本以为是条生财之门,然而门还没彻底敞开,就又关上了。 没有要回去弄午饭的意思,刘文黄老两口带着孙女坐在村委会广场的凳子上,离石凳子五米开外的水泥地上,晒着不少玉米,黄灿灿的一片,像是在吮吸冬日来临前,最后的阳光。 在刘文黄的日常安排中,只要没干活,那一家人中午的那一顿饭,就会省去。 “没用力气,就不吃了,晚上一起,土豆也顶饱。” 一年到头,刘文黄一家也吃不上几次肉,“没地方买,再说太贵了。” 只有等到儿子媳妇从外地打工回来,他们才能在食物上获得慰籍。可刘文黄的儿子也不咋回来,一年也盼不到一回。 一想到儿子,刘文黄叹了口气,用力扯下左边裤带上的小瓶子,瓶子里装了些烟叶子,是刘文黄自己种的,他小心翼翼地抖出一点儿,卷了卷,塞进了烟枪里。
-3- 66岁的刘文黄自觉身体还算硬朗,老婆子64岁也强健。平日里,老婆子裹着一根花布头巾,提着筐卖枣,是一群老太太里跑得最快的。 “不过,好多人听不懂俺说啥,还一个劲儿要上家里看看。” 老婆子有些无可奈何。 要上家里去看的大多都是边上露营过夜的游客,游客里很大一部分都是来拍照的小姐姐们。 她们带着摄影师,租上车,从全国各地飞来,极尽“手段”,由奢入俭。 2019年村里来了个旅游公司,划了一块靠近黄河的地儿,修了些帐篷样式的水泥小房子,在门口立起个巨大的水车,挂上个牌子,就成了北长滩自驾营地。为了得到这块地盘,旅游公司硬是把本来在这里的一户人家,迁到马路对面的山坡上了。 靠着这个营地,刘文黄家里也在去年,通了自来水。在后面的山凹凹里,竖起了一个巨大的黄色水箱,再经由裸露在外的管道,流进各户家中。 同时覆盖的还有网络,即便还不算稳定,时常丢失信号。可为此,刘文黄还是特意攒下个老年机。记不住电话号码的他,在那个看似像玩具电话的背后,细致地贴了一张纸,上面工工整整地写满了11个数字。 而这11个数字,暗示着老人和外界最重要的连接,纵然几近无人,可还有媳妇可寻。 “儿子不争气,欠了那些钱。媳妇也没说要走,这才去工地上打工,这才丢下孩子。” 刘文黄心里明白,自己的家事,也由不得自己。 唯一能由得他的“大事”,是遇到有些男性游客,昂首阔步参观完房子后,对放置在屋里正中央桌上的一尊毛主席小雕像,产生的兴趣。 “有人都出了5000块,让我卖给他,我说啥都没给。” “那能给吗?那可是毛主席。” 刘文黄每次遇到外人总会说上这么一段,毛主席雕像是有物可见,话语的真假却无从考量。 无从考量的还有刘文黄和剩下27口人的去处。通过社交平台,日益渐火的北长滩和北长滩沿线的这条道路—66号公路,让当地政府也嗅到了致富的气息。而如何合理合法又合情地迁走这些留守居户,成为了官员的当务之急。 这几个月来,政府派人不下来了10次。挨家走访劝说私自造烟的村子,总算劝走了3家人,可剩下的十来家人,像是铁了心。 “说是要保护我们的老房子,说是要脱贫,可也不给赔偿。我看就是黑了心,要搞旅游,赶我们走。” 刘文黄和村民不是不愿意走,即使给集中安排住所,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在残存的力气中,刘文黄找不到用以为生的生计。 “给我安排个扫大街的活儿,也成,可来人咋就不答应。” 刘文黄不明白,没有人有义务去解决这个问题,何况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
-4- 不一样的人,不止是劝说刘文黄的政府办事人员,还有这些“过路”游客。通过她们的手机,和大名鼎鼎美国66号公路重名的66号公路,也披上了皇帝的新衣。 在离村子几公里远,视野最好的一段公路上,政府模仿着,用白色的油漆在马路上,钩画出66两个数字。这样的logo,在小姐姐们的照片里,得以凸显,无声传播。 更有甚者,道路两旁摆放了一堆道具,用以给前来照相的游客服务。 “50块半小时,和摩托车道具随意拍。80元所有都可以拍。” “出大片,哈雷摩托私自造烟的村子,牧马人越野。” 举着相机在为一个姑娘拍照的男子,赶紧说道。 偶尔有大车驶过,都必须降低速度或是干脆停车,等待面前的拍照结束。“66号”的公路属性被渐渐抹去,成了照片背景墙。就像属于刘文黄的人生,也即将被抹去。 让刘文黄一家迁走,让整个村子剩下的居民迁走,也并不全错。交通的极其不便,村子在基本设施上,无法完善。 “没有医生,在村委会有个屋拿来做卫生室,市里头安排了医生来坐诊,没几天人就不来了。” “嫌太远,可不是有车吗?还嫌远。” 刘文黄不懂。 想要通过66号公路,进入北长滩,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自驾。市里过来没有专门的班车,遇到涨水,黄河倾泻上来的水,瞬间就会淹没进村的道路。这条唯一的道路,在汛期长时间处于水流之下,露不出头。而北长滩在道路被淹后,也不再露脸。 “还好有次出事,没遇到涨水。” 刘文黄记忆犹新。在几个月前的下午,他突然觉得不舒服,村子里没有医生,家里也没有药,连续吐了3回的刘文黄,跑到马路上寻求帮助,最终遇到两个好心的姑娘,带着他去了市里,送到了医院。 “医生说是食物中毒,不晓得是不是剩菜馊了。” “还好没花多少钱,输了液,住了一宿就回来了。” 从市里回来就不像出来那般容易,耗费了刘文黄一天的时间。最后一段路程,他在66号公路旁,问了几伙子人,才等到一个愿意带他去村里的师傅。 “我等她们照完相,挨个问,总算成了。” “这条路到底有啥好照的,是有个啥花花。” 虽然不懂,但刘文黄还是不免为此感到庆幸。 庆幸的远远不止于此,通了水的村民,不用再吃黄河水,一个村子的一口旱井,用尽全力滋养着枯瘠的画面,也到了退位的时候。 就像物质的丰俭悬殊之外,深陷山沟里贫乏的世界,和外界的纷繁有余,本就无法相互理解。 刘文黄和村民在意的是,离开,就代表着深不见底的支出。而政府在意的是,集中改善村民的居住环境,是脱贫的必需。 “在村子里,至少能活。走出去,还能成吗?” 刘文黄几乎每一天都会和邻居们“商议”,他们聚集在村子里最好的新式建筑下,背靠着“脱贫攻坚”几个大字,妄想找到解决的途径。 “可不是呗,人是多了,可和俺们有啥关系,一点好处也不得。” “80多的人了,还能搬去哪里。能走,早不就走了。” “走吧,还是回家,政府说是还会来人,回去等着。” 刘文黄阻断了这次无果的谈话,顺手牵起蹲在地上玩的孙女。深秋时节里,淌着大鼻涕的孙女没有穿袜子,踏着双拖鞋,拉着爷爷的手,渐渐湮没在快要褪去的夕阳里,犹余清冷的气息。 他们与打卡的姑娘们错身而过,一身裙装下,同样光着脚丫。 好在夜幕降临后,村子再次阒无人迹,就像从未被打搅过。
-END- - 写 作 之 星 - 图文 | 卓夕琳,青年作者。 “我故”故事练习生培养计划,详情请戳: 培养计划|加入“故事创造营”,你就是未来写作之星!
About us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