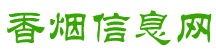|
时隔半月,村头的空气中仍然弥漫着淡淡的烟草被焚烧后的味道 汽车艰难地爬过浮桥,冲上河堤,简城村扑面而至。 这里显然刚刚经过一场打假风暴的洗礼。村头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烟草被焚烧后的味道;墙壁、门头、电线杆上,到处张贴着“坚决打击制售假烟的犯罪行为”等标语;从章化乡简城村学校飘出的喇叭声中,舞阳县政府的相关《通告》也正在被反复播放。 学校门口的斜坡前,停放着不少车辆,一些穿制服的人正忙忙碌碌。章化乡乡长宋朝选告诉记者,3月18日集中行动结束后,县里和乡里有关部门组织了一个四五十人的驻村工作队,巩固阶段性打假成果,协调善后事宜。 看得出来,简城村的生活有点寒碜。除了为数不多的两层小楼外,村里大多是砖木结构的房子,还有不少有裂缝和坍塌痕迹的土坯房点缀其间。而在整个村子里,记者甚至找不到一条像样点儿的道路。
或许是见怪不怪的缘故,村民们对外来车辆并不感到意外和惊奇,相反倒有几分木讷。在工作队驻地的斜对门,一群搓麻将的村民兴致正浓。 可能是见过“大场面”了,一个村干部模样的人快速跑到记者跟前:“我们村有点冤,机主都是外地人(襄城县和叶县),他们是租我们村的房子,一年才几十块钱……” 但该县相关领导在随后反驳了这种说法:外地制假售假者渗透和盘踞简城村的情况不假,但如果说当地人都没有参与也是不客观的。记者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位领导的说法。可以说,该村的每个角落几乎都散发着与假烟有关的信息。 村里不少住户关门落锁,其中有些据称是“被打掉的造假窝点,机器被捣碎或被没收了,人抓的抓、逃的逃”。
但余下的,依然够得上触目惊心。不少农户的门口、房侧和屋后,都堆放着成袋成袋烟丝,有的泼洒一地,有的还在冒着呛人的烟味;村里大大小小的池塘、水坑中漂浮着各种鼓囊囊的编织袋、麻袋,里面大多也是烟丝。“这些都是打假前村民从家里转移出来的,那些露天堆放的也被泼过水,不能再用了。”专卖办的工作人员说。 村后直达渡口的土路上,沿途也遗留有不少烟丝和成品烟。仅一处麦地边沟中,就倾倒有数万支的成品烟,有“帝豪”、“群英会”、“福音”等牌子,有的根本没有商标;河滩的沙堆上、水里,也能觅得见烟头、烟支和包装袋残片。 毫不夸张地说,整个村落,都被虚假的“烟”味严严实实地浸透着。 对舞阳而言,简城村像一个被割离的孤岛。
和平原地区的其他农村不同,在简城村很少能见到连片的土地,起伏的丘陵和时断时续的水脉将这里的农田切割得零零散散。 简城行政村隶属章化乡,包括简城、王庄、程庄三个自然村,2500多人,耕地1000余亩,人均约4分地,“糊口都是问题”。 正在打麻将的村民刘妮妮(音)告诉记者,她家4口人,有一亩多地,“去年打了五六袋麦子(约300公斤)”,而秋天的玉米则因为涝灾,颗粒无收。刘妮妮家的地连自己的口粮都顾不住私自造烟的村子,靠丈夫打工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刘的两个孩子早就辍学了,“上不起,他们也不想学”。 除了驻村的干部外,记者在简城村很少见到青壮年的男人,村干部的解释是:“在家守着吃不饱饭,都到外头的建筑队打工去了。”
然而有人私下里告诉记者,有些人看到中央台的节目后,“连夜就跑了”。 舞阳和邻近的县都盛产优质烟叶。一个老舞阳人回忆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简城村人就有造烟的历史,只不过那时是为了自己抽,“90年代后,市场经济了,他们就开始往外卖”。 据说,在“3·18”之前,这里甚是“繁华”。一进村,就能听到机器的响声,“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只要有包装,啥烟都能做”,一台卷烟机一天能生产一二百箱香烟,有时候一台机器一天就能挣万把块。但据知情人讲,发财的机主是极少数,大多数人也就是打工挣个辛苦钱,村里贫富差距很大。 假烟从河边经过渡船、三轮车或面包车转运到舞阳县城,然后再从县城发往全国各地。央视记者在暗访时发现,简城村每天运出的香烟数量惊人。 或许正是源自这种生存的重压,村民们开始了扭曲的“自救”。 天然的地理屏障给制造假烟提供了“地利”,简城村历史上也有与相邻叶县、襄城县通婚的习惯,这边打假风声一紧私自造烟的村子,连人带设备都可以转移到周边的亲戚家去,这就是“人和”。打假中的“属地原则”对这种三市交界地带也确实无可奈何;而时下不少行业的信用缺失和假货横行,就自然成为造假者的“天时”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