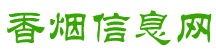|
乡村炊烟 杨小梅 你是否凝视过一缕炊烟的轻舞飞扬?一如你凝视母亲的笑脸、母亲的眼泪? 母亲的笑脸盛开在平常的日子,母亲的眼泪流淌在时光深处。母亲有多老,村子就有多老。母亲老了,村子也老了,有人走了,有人来了,走了的人,留在了村里,来的人,离开了村子,村庄里的炊烟没有人看了,荒草占领了村道,有的爬上了树,薅草喂牛喂猪的人走了,草就爬上了房顶,钻进了烟囱,就是钻进了烟囱,也燃不起清香的、暖和的炊烟了。 炊烟升起,日子开始。刘禹锡在《竹枝》一诗中写道:“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描述花木掩映中,升起了袅袅炊烟,必是村民聚居之处。人烟,即是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人和烟火相生共长,没有烟火升腾的日子,人就退场了,没有了人烟,村子就荒芜了。谁家的烟囱不冒烟了,这家人就散了,走了,不再回来了。 炊烟升起,生活开始。“良顷千里,日食一升。”雾气蒸腾的厨房里,母亲操劳着琐碎的日子,有母亲在的厨房,是天底下最好的厨房,母亲把对一家人的爱和希望都倾注在一饭一粟、一菜一汤里。吃饭穿衣量家当,没钱买煤的日子,柴禾相较于粮食,同等的重要,农闲时节拾柴的队伍,其浩荡之势、热闹之态,可与年关赶集的场景相媲美。拾柴人一去几日,结伴吃住在山沟崖畔,吃尽苦头,才换得一车一车干柴拉回家,也才能在门前摞起大柴垛。谁家门口没有大柴垛,人家就会笑话他:“拐穷的你看连个戳鼻子棍棍都没有么,扎哈拐倒槽鬼茬,唉,咋处呀!”笑话归笑话,自己的罪还得受,免不了的挨饿受冻。柴火回来了,暖和的日子跟着来了。“椿树有油哩,枣树有牛哩”,哪个柴烧起来火旺,哪个柴烟大,什么柴禾烧什么饭,都在母亲们的心里装着,烙馍烧麦草、麦衣和蒿子,烟大火小,烙的馍软和,炒菜下面蒸馍煮肉烧的劈柴,火大烟小,势头足,“紧锅馍慢锅肉”,蒸馍时要大火烧,馍馍凭着一口气,“气”烧上来了,馍才好,蒸馍时如果烟囱里的烟慢腾腾的,馍馍自然好不了。煮肉要慢火炖,才能煮出味道来,肉在锅里香,炊烟在村子里香。
正午的太阳热辣辣跳进村子,落在树梢上,投下一地阴凉,站在窑顶上,洒下满院子金黄,爬进窗户里,涂上一屋子安详。太阳走到哪儿,哪儿就喜笑颜开,日子跟着太阳跑,太阳跑累了,钻进云层里去偷懒,可日子过得再累,也不敢偷懒,再忙活的日子也得生火做饭,烟熏火燎的日子,过不腻,过不烦。天晴的时候,炊烟被阳光抚摸着,贴着崖壁打盹儿,慢悠悠聚成一根线,袅袅婷婷地钻进云朵里。阴雨天,烟也怕冷,缠着人不肯离开,挑逗人的鼻子眼睛,惹得人家鼻涕眼泪的。 当家家户户的窑洞的烟囱里飘出炊烟的时候,放羊、放牛人的吆喝声,喊自家孩子回家的呼唤声,鸡鸭猫狗扯开嗓子讨食吃的聒噪声,牛羊归圈呼儿唤女的叫声一齐聚拢过来,汇聚成“风萧鸾管”的乡村交响乐,把整个村子的心都唱活了。小脚的老奶奶系着围裙等在大门口,看着儿孙们走进家门,数着牛羊归圈、鸡鸭上架。 吃过晚饭,天色尚早,男人拿上旱烟锅,女人拿上针线活,没有号令,不约而同地聚在村子中间的“大树嘴嘴”上,说是“大树嘴嘴”,因村子中间一处平台突兀在崖前而得名,平台连着村道,背靠饲养站的院墙,崖下是大片的洋槐树林。漫山遍野的洋槐树,花开时香气四溢,一大片雪白缠绕着“大树嘴嘴”,冬日繁华褪尽,太阳懒懒地挂在天空,照着“大树嘴嘴”的每一寸土地,因为在村子中间又背风,无疑是村子里最为合适的“休闲娱乐场所”,更是小村所有或纯净、或荒谬的“文化宣传”集散地,家长里短、世事荣枯、偷鸡摸狗,那些被人们咀嚼了无数遍的故事,听着石碾吱吱呀呀的碾米声、旷远的狗吠、慵懒的鸡鸣,裹着旱烟锅里飘出的烟草味,合着烟囱里飘出的草木香,长了翅膀似的越飘越远。 冬天的炊烟和其他季节的不一样,冬天的炊烟跟着人走,其他季节的炊烟跟着风跑,跟着人的烟在雪地里打旋,在雪天里开花,开出的花儿和雪花肩并肩落下来,跟着雪地里的脚印深一脚浅一脚的踩进院门,回了家。再厚的雪,再冷的天,在娃娃们的眼里,是一顿饱饭的事,在男人的眼里,是一锅旱烟叶子的事,在女人眼里,就是有柴没柴的事。有柴,就能放火做饭,也才能飘起炊烟,烟囱里冒烟了,一天的日子才开始了,上学的孩子叫醒了沉睡的村庄,男人们肩上的水桶吱吱呀呀一路从家里唱到沟底,冒着热气的泉水边,男人们点上旱烟锅,蹲在泉边抽烟抬杠,斗嘴耍贫,完了挑上清的能看见桶底的泉水私自造烟的村子,说说笑笑地回到家里,他们的女人早已生火热好了馍,男人们就着咸菜吃着玉米面角角馍,喝着女人熬好的罐罐茶,惬意地打个饱嗝,便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女人拾掇停当,包上五颜六色的花头巾,担上笼筐去扫落叶,落叶塞进灶火眼、炕眼,飘出来的烟都是树叶的香味。
夜黑了,村子要睡觉了,煤油灯点亮了窑洞,男人靠着炕头的栏杆抽旱烟,女人抱柴烧炕,烧炕用山上割回来的蒿草败叶,煨的是干牛粪私自造烟的村子,火生着,空气中弥漫着草木和干牛粪烧着以后特有的清香(是清香,牛吃的是草,牛粪自然有草的味道,一点不假)。没有“霾”的日子,烧炕做饭都用柴,炊烟弥漫,天还是蓝的,水还是甜的,清新的泥土里长出的庄稼也是活蹦乱跳的,裹着炊烟满村子跑是不用戴口罩的。遇到阴雨天,风不利,烟就罩在村子里不走,村子就像钻进大布口袋一样,密不透风地温暖着。
电视没有普及的日子,如果逢上村里放电影,夜里,十里八村的人都会跟着一场电影狂欢。夜是真的黑,黑到你看不到自己伸出去的手,路上的人,有的拿着点了火的草绳赶路,用夏季割的白蒿拧成手腕粗的草绳,晒干点着了,火小烟大不烧手,既能照亮还能熏蚊虫,放电影的地方,荧幕上人影绰绰,笑语盈盈,场坝里星火点点,烟雾腾挪,如梦如幻。 炊烟升起,生活有了根。飘着袅袅炊烟的村子,它的灵魂是饱满的,我们的乡愁也是鲜活的。 杨小梅,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人,企业职工,文学爱好者,县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有文字散见于杂志、报刊和网络。 出 品:灵台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来 源:灵台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