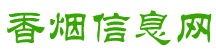|
原创 曹乐溪 AKA桃叨叨 拍《隐入尘烟》,兜里只剩不到2000块钱 桃友记Vol.14 作者/曹乐溪 编导/小 谭 时隔近半年,《隐入尘烟》终于与观众见面。 采访李睿珺是在冬天的尾巴,那会儿主演海清还没因为封“神”事件轰动全网,电影资料馆人潮汹涌,多是冲着导演作品四部连映慕名而来的观众。 李睿珺坐在签到台,敲打着即将发在豆瓣上的小作文。他习惯手写剧本,因为这样就不用在星巴克跟人家抢电源,而且随时随地都能掏出笔记录灵感。 “手机太慢了,我写字很快,有时打字跟不上大脑运转。反正字写成什么样,只需要我自己认识就可以了。”
从《老驴头》《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路过未来》到《隐入尘烟》,在李睿珺的作品中,你总能窥见乡土与诗意、现实与浪漫交织的丰富底色。 《隐入尘烟》的故事在脑海里酝酿了五六年,李睿珺开始思考土地与生命的哲学:麦粒被收割,是死亡还是新生?被大众忽视的个体,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两个农民最普通而纯粹的爱情,也许源于暖水瓶和电报鸡窝? “拍电影就是你不断发现这个世界,以及发现自我的过程。”由冬入夏,四季轮回,在电影拍摄的一年多时间里,李睿珺也经历了投资因疫情落空、临时找人找钱等一系列复杂境遇。 电影中老四与贵英说,啥人有啥人的命数。作为一部文艺片,《隐入尘烟》的排片率低几乎是必然,能有多少人看到、又如何评价,李睿珺觉得这是观众的自由。
自己的工作如农民,只负责收集散落的语言化成文字,通过镜头结出电影的果实。 所以这部电影的命数,亦交给土地与时间。 以下是李睿珺的自述。
播种 《隐入尘烟》的成本不算低,因为要拍一年,希望不要给老板们赔钱,这样才能有继续下去的可能性。
一开始本来是有资方答应投了,但因为疫情爆发,整个电影院都关了,积压的电影不能回收,影视公司还得支付高昂的房租水电、员工工资,资金就出了问题。 我们就说拿自己的钱垫着先拍起来,反正要拍5次私自造烟的村子,先拍完一期我们再来找第二期的钱。拍电影一直都在找钱,这种状态对我来说已经习惯了,以前就是自己攒点钱就拍起来了。
这次的疫情是谁都不能预料的,你说我粮食富裕一些的时候借给你可以,现在大家都不富裕,你也已经看到人家的难处了,资方也养了那么多口嘴要吃饭,你肯定不能说必须给我怎样怎样。 拍到第3期的时候需要拍22天,实在是我们都问遍了,辗转联系到嘉映影业覃总时,我和(制片人)张敏两个人,身上只有不到2000块钱,连一张机票都买不起。 我们坐了十来个小时火车来北京,剧本都没有,我就给覃总口述了一下故事,覃总说先别说了,我们先打钱吧,打钱你先去拍,剩下的钱我们也帮你找着。 监制与覃总为电影前前后后付出了很多精力,没有他们,可以说就没有今天的《隐入尘烟》。这个“孩子”很幸运,一路上总能遇到能给它精心照料的人。 现在他们都看过成片了,给了很多鼓励,但我也不好意思问你们真的喜欢么(笑)。 说实话,花一年时间拍一部电影很奢侈,相当于它要用两到三部电影的钱和时间,你要反复不断地开机、关机,可能还会吃力不讨好呢。 这样的电影项目可能一般公司一听就拒绝了,觉得风险很大,投资完全是纯情怀。他们也预计片子不会大卖,只是说支持一下这部不太一样的作品,为市场提供一些更多样的选择性。 在家乡拍戏很多年,有乡亲围观是很正常的,乃至我们县都知道我在拍电影,也间接带动了家乡的电影教育。 我就是在花墙子村出生长大的,在我之前,我们高中没有人考过传媒类院校。2009年回乡去拍《老驴头》,所有人都觉得很可笑很荒诞: 你小时候在村子里光着屁股跳水的样子,大家都见过,现在突然回来说我要拍电影、做导演,我要让你们参与表演,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只看过电影,从没见过有人拍电影。
《老驴头》入围釜山电影节,那时网络还不发达,村子里只有一台电脑是商店老板的,就是《隐入尘烟》里老四和贵英去买东西的那家商店。 但当时报纸版面和手机报会有消息,很多人都看到了,再到《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时,就有很多村民报名来演。
《白鹤》当年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在央六播出,那个平台对他们来说是很神圣的。大家之前觉得我们长得也不好看,我们村子不漂亮,语言也很土,你为什么要拍? 但在电视上看到时,会觉得其实我们并不丑,我们的村子为什么在电视上会那么漂亮(笑)。 在这种过程中,大家找到了很多自信,乃至他们认为,如果我被一部电影拍下来,那么若干年后我不在了,但我的形象依然还存在。 他们变成了我们县最懂电影拍摄的农民,去任何一个地方买东西,都会有人认出来。在坐40公里车回村的路上,大家聊起电影,他们会变得滔滔不绝。
像《隐入尘烟》的主演是我姨夫,他们一家从2009年开始演电影,这部片子里的三嫂是他生活中的妻子,结尾拉着两头猪出现的是他儿子,在《水草丰茂》里演一个小喇嘛。
姨夫的儿子在剧组做摄影助理,女儿大学本科是学油画的,毕业后去电影学院读了一年的影视化妆造型,现在在剧组做化妆师,这部电影的造型就是她做的。 现在,我们县里已经有了我同一个学校的师弟师妹。 假如有一天,这个村子里再有一个孩子长大,说他想要去拍电影,不会再遭到全村人的耻笑和讥讽,他和父母说我要学电影时,也不会再像当初我父母一样那么不理解。 我觉得,这都是拍电影带来的一些变化。
生长 《隐入尘烟》是关于爱的,我当时就想我们能不能做两个容易被大家忽视掉的人物,最最普通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把“妆”卸掉、回归爱的本质后,那不就是生活的点滴么,平淡如水,清澈见底。 一开始两个人可能并不是爱情,直到贵英去桥头接老四,她颤巍巍地掏出暖水瓶,像是从自己心脏里拔出来一样,他拧开发现还是热的,马上就被感动了,语气也变软了。
老四把买来的长大衣给她披上,说你以后出去就穿这个,因为她有尿失禁的问题,穿着能保暖又能遮住(屁股)。从这里开始,两个人对对方有了新的认知,它不再是搭伙过日子的状态。 那场戏真的很冷,不停地在换热水。晚上我们先是拿吊车把灯布好,等天黑了拍,后来发现不好看,最后就说用抢天光的密度吧,每天有15-20分钟的时间,既是黑暗的,但远处层次都能看到,那种自然景象是靠打光打不出来的。 我们抢了三天,后面几乎所有的夜戏都是这样靠抢密度抢出来的,尽量少用人工光的干预,那种时刻是最美的。 电影中老四用麦子给贵英“送”了一束花,他没办法去找一束鲜花,就用最简单的方式,将麦粒拼成花瓣按在手上,说我给你种了一朵花,你以后跑到哪里都不会丢掉。
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不是爱情,在我看来它是更广义的爱,这里面有爱情。 贵英与老四从彼此身上,找到了前半辈子没有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尊重,关心和在意,这重新唤起了他们对于生活和很多事情的希望,也唤起了他们爱的能力。 电影里有很多关于生命的部分,老四向乡亲借了10个鸡蛋,我们小时候没有母鸡,就用电灯的热量孵化,我们管这种鸡叫做“电报鸡”。
长期靠电灯去孵蛋,纸箱上要扎小窟窿眼散热,不然热量过高把纸箱烧着了,这些是农民在生活中积累出的生存哲学,而我从这些日常里感受到了浪漫的东西。 你想那个灯在里面突然射出来,屋子里面像一个摇曳的舞厅一样,让贵英看到了生活的诗意。她突然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人生境遇:再卑微的个体,ta的生命也可以是绚烂的。 老四其实是无意识的,他一插上电,没有想到她没见过(这样的场面)。看到她那种欣喜与感动,他就自然地摆弄着灯,这也是他很含蓄表达他爱意的方式。 贵英用草编了一头驴,问老四说像不像我们家的驴。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贵英看到老四能对一头驴那么好,就觉得未来他对我也会不错。 老四说还是做草编的驴好,因为它不用吃东西,就不用被人使唤,他感受到驴也感受到自己的命运。 他没有把驴简单当做一个牲畜或私有财产,而把它视为生命中的伙伴。这是因为老四和贵英在生活日常里等级好像比别人低一点,所以看到麦地里不能左右自己生命的麦苗和驴的时候,他们认为我们是一样的,都是大地的孩子。
生命有各种偶然和意外,不是每个人的生活都能按我们所想的进行下去。他俩在一起本来就是一个意外,当你一直没享受过爱的时候,你不会认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但拥有了又再失去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的。 我们要如何去面对这种生命中的意外和偶然?任何人的生命中都会有悲剧性的时刻发生,不可能有人一帆风顺,这就是生活的真相,既美好又残酷。 活着就是喜剧,死亡就是悲剧么?我不那么认为。麦子被收割,麦粒是死亡还是新生?土变成砖石又变成墙,最后回归尘土,你能说它没来过这个世上么? 只是在某一刻,生命以不一样的形式存在罢了,它隐入到日常生活中,隐入到我们所谓的烟火气中去。 对老四和贵英来说,这一刻该享受的我享受到了,对他们来说死亡并不是痛苦的开始,有些人在选择死亡的时候,是很幸福的。 就像电影里两个人种地,老四跟在后面播种时开玩笑说,像不像把你的脚印种在地里了。贵英说那我不想种下去,就像麦子一样哪里都不能去,只能被驴啃。 人是可以自由走动的,虽然看似在别人眼里他们是不幸的,但他们觉得自己比麦子、庄稼要幸运地多。 生命就像麦子一样,从麦粒回到麦粒,并不一定是结束。
收获 《隐入尘烟》中拿结婚照当遗照,就是因为贵英没有一张照片。 我2009年拍《老驴头》的时候,村子里的老人没有遗照,去世后会拿身份证去县城照相馆放大一张做遗照。 老式身份证就是黑白镀了膜的,不像现在这种彩色有水印。有时你放大再放大画面会很虚,甚至你能看到防伪标志,“长城”压在他们的脸上。 《老驴头》时我请一位老人来演老驴头的父亲,他在电影中的演出是以遗照形式出现的,只在梦境里出现了一次。 我就给他拍了张遗照,洗了三张,他说我特别喜欢,我还没有遗照呢,你能不能送给我一张,将来当做我的遗照,他觉得很满意。 于是我们拍这部电影时,不断有人来找我们说给他们拍遗照。 乃至2012年拍《白鹤》时,主演是我的舅爷爷,临走时他说能帮我再拍张遗照么。我说09年不是拍了么,他说三年过去了,我长得也不一样了,再帮我拍一下呗(笑)。我就给他和舅奶奶又拍了一次。
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我觉得贵英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可能没有一张像样的照片,但她会永远活在那个男人的心里面,她比那些有无数照片的人可能更幸运。
就像电影中那些桥头的女人不解为何这样一个人,还会有人如此去疼她。旁边人说,那你为什么当初不嫁给老四,你要是嫁了,他也照样疼你。贵英与老四,也唤起了这些人对于爱的重新思考。 这两个人在别人眼里可能是傻子,是传统农耕1.0时代的落后象征,但他们身上还保留着那种人类最原始的诚实、守信与爱。这些都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只是有的人在“进化”的过程中,不断丧失掉了。 其实我挺惧怕“成熟”这个词。它意味着某种固化,我们让一个孩子变得成熟,就是变得比较乖、被归驯。作为创作者,我会警惕所谓的成熟,是不是意味着思维变得程式化?这不好说。 2017年《路过未来》上映时,大家觉得你是不是要转型做商业片,到城市里拍这样一部电影,是“社会新闻的拼贴集合”。 误解是构成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一部分,很正常。《老驴头》的男主角出生在民国时代,建国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拥有土地可以自主耕种。但2009年实行土地流转政策,大部分土地集中起来耕种,每亩地拿土地补偿金。
老驴头不想这样,那时候社保医保没有那么高,儿女打工不回来,你只能依靠土地。但子女觉得土地对我们来说是累赘,生产的粮食又卖不了多少钱,两代人的矛盾就产生了。 改革开放40年,抛弃土地到城市务工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能在城市里生活么?他们的子女怎么办?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持续性关注的命题,拍《路过未来》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说得简单粗暴一点,它就是《老驴头》的续集。 但你不能要求每位观众都看过《老驴头》,他们自然会觉得你前面拍乡村,现在拍城市,初心变了。他们对你也会有自己的期待,你打破了我们对你的想象、对你的需求。 但一个导演是不可能满足于任何观众的,ta的创作只服务于自己的内心和对周边世界的观察思考,我不可能成为被他们定义的李睿珺。 有观众觉得喜欢,有些观众不接受,我觉得都很正常。电影本身已经是一种很集权的方式,大家被强制关在一个空间内,不能打电话要看完这个东西,你做的是一个表达,那你为什么要束缚观众的表达呢?这是观众的自由。 我记得我2006年拍《夏至》,宁浩导演找了250万拍《疯狂的石头》,我就觉得那是一笔巨资! 那时候都是自己借钱拍,现在有这么多电影节创投,导演处女作就拍几千万成本的,有很成熟的第六代导演愿意帮他们做监制。我们那个时候想都不敢想,也没有这样的机会,现在制作环境也好多了。 我觉得影院不会消亡的,就像电视诞生时,很多人觉得电视会取代电影一样。当然未来家庭影院和网络会是主流趋势,但总有“深度玩家”会在更专业的赛道里去玩。 即便电影再式微,最后也会变成类似俱乐部、深度体验馆一类的东西私自造烟的村子,让大家在大银幕上感知故事节奏、表演的细腻层次,情绪会波浪式地递进到场域的每一个人。在家观影,这种互动会变弱。
轮回 我年前一直在忙,没有时间去电影院,最近一部进电影院看的是耿军导演的《东北虎》。前段时间在老家,县城里的电影院不是特别标准的电影院,观影感受不太好,宁可回北京来看。 现在大部分时间在北京,拍电影时回家乡。每部电影从筹备到拍摄会呆很长时间,家乡和自己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你曾经熟悉的老人都逐渐离开了世界,村子里你认识的人变少了,新出生的人你不认识他,他不认识你。 拍《隐入尘烟》时,驴冬天怀孕了,后来小驴出生,剧组每天都有人把小驴抱着,我这次回去看,小驴长得比妈妈还大了。 驴就是姨夫家的驴,跟我也算半个“亲戚”了。因为拍摄时已经怀孕,它很听话,等生完孩子就没那么听话了。拍摄的时候好多人围观,就和姨夫说,武仁林,你家这头驴就是为电影而生的!其实他们不知道它那时候怀孕了(笑)。 每个人在不同阶段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变化,对生命和对周边人的理解不一样了,想拍的东西也发生了变化。 一直说导演是处理时间和生命命题的人,其实农民也是如此,本质上我们是一样的人。 有时会回忆起拍《隐入尘烟》的日子,海清老师干完农活,靠在一个被锯掉的树桩上睡着了,我在那儿改剧本。 我就在想农民将种子埋入土地,静静陪伴一年之后收获粮食,我做的工作也只是把那些散落的语言变成文字,播撒下去,它在时间的长河中,通过镜头结出了果实。 “种”下一部电影会怎样?可能收获了一些观众的目光吧,也可能会有情感。 一些观众也许认为《隐入尘烟》将苦难浪漫化,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在我的理解中,再残酷的生活也会有爱的存在,再卑微的个体也拥有对美的追求与向往,这很正常。 我就是如实记录两个人的生活,呈现他们的变化,难道说他们不配拥有爱么? 有一天我下楼时,电梯间有一位小伙子匆忙闯进来,赶着去送外卖。一出门我发现他电动车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女性,原来是他女朋友陪他一起送外卖。 我就很感动,一直等着小伙子出来,看他们再去下一家。当然这可能也是我的想象,她也许就是从外地赶来看他,但在那一刻,我觉得这就是对爱的诠释。 这些现实中发生的事,会变成创作灵感,有些时刻是你永生难忘的,它一下子击中了你,不需要言语。 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生活里特别无趣,从来没有给张敏送过什么礼物,真的。可能是习惯了吧,我会觉得如果生活中要送她个什么或者说我爱你啊,怪怪的,说不出来也做不到。 前些天我从家走的时候,我妈在楼下送我,她流泪了。我心想我应该过去给她一个拥抱,至少安慰一下,但我没有。典型西北人,即便想到了也没法表达。 关于对《隐入尘烟》的看法,我没跟张敏探讨过,也不好奇她怎么看这部电影。因为她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故事,并且参与了整个制作。有些话她不说,你就没必要去问,问是没有意义的。 或者你硬要问出来,那个东西有时也不一定是她真心想说的。尤其张敏,她是我老婆,即便是不好她可能也说还不错,也许只是一个安慰而已,对吧?她能说什么呢? 当然,那也是她爱的表现嘛(笑)。 (喜欢本文的话,点击顶部【AKA桃叨叨】关注,这里不缺好故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