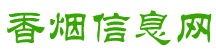|
她茫然地坐在时代广场前,手里拿着一包香烟。 她不知道为什么要买那包香烟。她既不会抽,也想不到要送给谁。她父亲是不抽烟的。那个日本人也不抽。他倒是抽的,但她已经碰不到他了。 烟盒是大红色的,那种非常俗气的大红,还有几个金字。买烟的时候她有点不知所措。她没想到买包烟那么难。香烟的价格又千差万别。相比起来,倒是买衣服容易得多。只要贵的店不去,看不顺眼的不看,看中了等着它打折,一切就水到渠成。逛商店是女人天赐的消遣,里面有说不出的乐趣。买香烟,显然是男人的事。虽然这个年头女人买包烟已经算不上大逆不道。但她依然感到十分别扭。尤其是那家便利店收钱的老头儿看她的模样,一副自以为是的腔调,对她虽谈不上冒犯,但明显有意见。令她感到恼火的是,她对那种腔调居然有点心虚。 “老土,没见过女孩子买烟吗?!” 好了,烟已经到手了。够便宜,十二块八。也不知道是不是便宜。她找不到参照物。比什么呢?体积上,比起肥皂好像要贵一点,但肥皂重。比起一包维达牌餐巾纸要便宜。但餐巾纸比较轻。她寻思了一会儿,觉得这件事让她有点头疼。香烟这种东西一直是游离在她生活之外的某种习以为常之物,就像豪华轿车和建筑工地,天天看到但视而不见。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吗?男人。对,男人。她想着就微微笑了笑,觉得这个类比非常聪明。 还有半年就要毕业了。接下来呢?找工作,找男人,结婚,生孩子。再接下去呢?工作,买菜,养儿育女,配老花眼镜。能想起来的就这么几件事。生活就是这么几件事。偶尔回忆回忆过去,出去旅游几次。她想起和他见面那次一起去徐家汇中心绿地玩,坐在人工湖畔的木亭子里。那里有两只怪模怪样的黑天鹅,还有一群白鹅。湖里游弋着几只玩具遥控船,把白鹅通通赶到岸上,而黑天鹅则若无其事地游来游去。那时她突然自作聪明地对他说,你看,黑天鹅和白鹅就是不一样。那群白鹅在那里唧唧喳喳,整天讨论的是青菜多少钱一斤,胡萝卜多少钱一斤,而黑天鹅呢,却在思考圣雄甘地和***到底谁伟大之类的严肃问题。他听了哈哈一笑,说没想到她居然那么聪明。 他哪里认真试图了解过她呀?她一直这么认为。所以就随口说出来。他听了什么都没说,眼睛一直望着湖面,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烟已经在手里了。生平第一次买香烟或许也会是最后一次。为自己某个说不清的问题买香烟。烟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关于香烟的广告到处都是,但没一个明着写上“香烟”两个字的。每包烟上都写“吸烟危害健康”,但烟店到处都是,比澳柯玛投币机还多。人为什么要抽烟呢?她感到迷惑不解。当然,这个世界有太多她想不明白的事,包括他,那个喜欢独自到处旅行的奇怪男人,似乎整天过得悠闲自在,也不考虑怎么赚钱。父母是不是为他买了房子,安排好如何娶妻生子之类的问题?她想起和他吃饭时她曾说过一句现在没房子谁跟你啊,他连理都没理。好像这是不屑考虑的问题一样。这让她微微有点失望。她想问这个问题是带有某种企图的,甚至还有一些潜意识里的暗示。当然,这是在潜意识里的。她已经有了算是比较正式的男朋友了,那个日本人。这他也知道。所以他一定不会留心她这句话的意味。以前他就没怎么认真地听她说过话,现在一定更是当做一阵耳边风了。 好了,既然烟已经到手。就拿一支看看吧。她找到了塑料纸的揭口,捏住,轻轻一扯。塑料纸盖就落在手里了。这倒是方便而轻巧。如果餐巾纸包那么容易打开就好了,她想,其实比较高级一点的餐巾纸打开也是利落而轻巧的,那种一块钱一包的就不行。而那正是她一直用的。倒不是成心图便宜那几毛钱。每次去街边的小货柜买餐巾纸时售货员总会问一句要一块的还是一块五的?她总是下意识地要一块的?这几乎已经成为习惯。五角钱能买什么呀,但能省为什么不省呢?她对自己辩解道。 他曾对她说过,她是个好女孩,是那类让人想结婚的女孩。她不知道这句话算不算是种恭维。有时晚上照镜子,她会注视着自己的脸很久,一边想他的话。镜子里的女孩算是美丽的,对此她还是有自信的。从小到大,周围的每个人都会说她是个漂亮的小丫头,他也曾说过。镜子里的女孩正是最年轻的时候,染着红色的头发,皮肤光洁细腻,额前梳着平平的刘海儿,脸圆滚滚的,有两只大眼睛。她觉得那个女孩很可爱,就对她笑一笑。女孩也对她笑一笑。随后就叹气了,“我到底算不算漂亮呢?”她问自己。她的朋友说她长得有点像王菲,又说她长得有点像周迅。“***像嘛。”她曾为这件事在和他吃饭时抱怨过。他听了只是笑笑,并没有回答。其实,她很希望他能肯定地说一句“你很漂亮”。这样的话女孩子是听不厌的。虽然被这么夸奖她一定会故作矜持地说:才不是呢。但女孩子不就应该这样吗?他不懂。他怎么会明白。那个日本人就知道,每次都会嬉皮笑脸地说上几遍“卡娃宜”。无论是她换个发型,或是穿上一件漂亮的衣服。想到这里,她心里就有点甜蜜蜜的。但随后,又会有点怅然。他怎么不会说呢? 她把烟取出来了,细细长长的一根,夹在手指间很舒服,掂在手心里却轻飘飘的。香烟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仔细打量之后,她发现那短短的一小段黄纸头包的烟尾巴是用海绵做的。洁白柔软,表面像是敷了一层细细的糖。“这就是过滤嘴吗?”她暗忖道,想象不出它有什么用。“或许是叼在嘴里舒服些吧。”她自作聪明地解释道,之后就轻轻地捏了它一下。 他会抽烟。她知道。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会抽烟呢?但他从来没有在她面前抽过。不知为什么。她当然也不喜欢男孩子抽烟,对身体不好嘛。除此之外,烟的味道也很难闻,又呛鼻。真不知道那些男人为什么要抽它。在他们吃饭的时候,旁边桌子上的两个男人在抽烟。烟雾飘过来,令她感到不快。于是她就说了一句:“两根大烟囱。”他听了也只是笑笑。他总是这样。其实他们见面时,他们都是各说各的。对于他的话题,她也只能笑笑。那些话题离她的生活很远。比如计划去登雪山,一次翻山越岭的徒步旅行,还有西藏喇嘛庙里的酥油灯。这些东西从他嘴里说出来,令她既着迷,又遥远。她记得几个月前他曾给她写过一封示爱的情书。那时他还不知道她已经有了男朋友。在那封差不多五百字的E-mail里,他表示终于发现她才是他需要的女人。他赞赏了她美丽的手和美丽的脚。并说这表明她拥有一颗细致而聪慧的心。他还说在最后一次见面时,她背对着他挑选十字绣,他突然觉得眼前的这个女人最终会成为他的妻子,为他烧菜做饭,生儿育女。那一刻,他甚至有拥抱她的冲动。这些文字令她脸红耳热,心突突地跳。她回完那封E-mail时,已是凌晨四点钟了。她抱着枕头坐在床上,一直无法产生睡意。她拒绝了他,因为她已经有男朋友了。她还在信里写到,我们总是在对方热恋时爱上对方,的确是可惜了。 她出神地把玩了一会儿香烟。天已经暗下来。晚风徐徐吹着她的脸。她感到很舒服。这个冬天并不冷。已经有好几个冬天都是那么暖洋洋的了。她回想起小时候,曾经在睡觉前让爷爷盛一碗水放在窗外,等第二天早晨,就变成了一块圆团团的冰。那时的冬天好像总是很冷,夜里的西北风呼呼地吹着,让她觉得有一个暖和的被窝很幸福。而现在外国人买烟的价格,已经没有那种幸福感了。冬天怎么不冷了呢? 她和他是高中同学。确切地说,是高三的同学。那时文理分班,她选历史,他选地理。两个科目合成一个班上课。他就坐在她后面,隔了一条走道。那时,他是学校里的名人。在她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他游手好闲,但成绩却总是第一。还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不过最后的头衔有点名不副实,他从来不组织什么活动,连团费都不收,她真想不通这样的人怎么会当上团支部书记的。但即使这样,同学和老师也对他恭恭敬敬。没有谁提出过要撤他的职。因为他实在太厉害了。 想到这里,她就微笑了一下。他曾说她是个讲究实际的女孩。整个高三,总是板着小脸,拼命地读书。“像个严肃的小哲学家。”她想这是实话。她是很实际,普通人嘛,不实际点怎么行,又不像他,既能通过音乐学院的考试,又能通过正规的高考,最后,还因为一次国际奥林匹克竞赛而被保送进大学。这些在她看来是匪夷所思的。现实好像从未对他产生过影响,他可以随心所欲,又能左右逢源,进入大学后,还出了本书。她还记得他在送给她的那本书的扉页上写道:请大小姐批评。这是按她的要求写的,还曾一度是她向朋友炫耀的资本,带给她不少快乐。凭着女人的直觉,她几乎可以肯定他会成为一个人物。超乎现实的,却是激动人心的。他的未来一定会非常精彩。不像她,以前就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墨守成规,平平淡淡。 “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她想,一边又轻轻地叹了口气。 六点.下班的时间。一些穿着职业服,挎着小皮包的女人步履匆匆地在她面前走过。她们一定是赶着回家。做晚饭,给孩子复习功课,等孩子睡下后,再看看电视,和老公说一会儿话,随后洗澡睡觉。这就是这个大都市里绝大多数年轻女人的生活。半年后,她也和她们一样,相夫教子,渐渐变老。时代不一样了,生活却差不多。每到周末时,或许会和几个朋友出门逛逛街,去星巴克喝杯咖啡。说说彼此平淡无奇的琐事。到了国庆长假,和丈夫孩子去某个地方旅行一次。关于未来,她脑子里就这些东西。她甚至可以想象出十年后她的模样,就像十年前她能想到现在的情景,一切都会按部就班地出现,平平稳稳,波澜不惊。 到底什么是生活呢?她歪着头想。就是过日子吧。一天又一天。睁开眼睛,呼吸空气,说说话,吃吃饭,吵吵嘴,睡睡觉。高兴的时候就笑笑,不高兴的时候就板起脸。像她这样正正规规毕业的女大学生,是不用太担心生计的。丈夫呢?会是那个日本人?现在他们正在交往。和其他恋人差不多,情人节会收到玫瑰,平时会接到电话,一个星期约会一次。她曾对他说过,她其实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中规中矩。毕竟时代不同了嘛。她和其他女孩子一样,既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坏。她不知道他会怎么理解她这句话的意思。会想到些什么?对于对方是日本人,他一定是受了些刺激的。她看见他得知此事后脸马上就低了下去,还说了一句:“你不怕被爱国同胞骂死?”听到这句话,她也有点脸红。这不是第一次有人对她这么说了,她的朋友,还有大学时几个要好的男同学,都说过类似的话。言外之意,仿佛她就是贪图了对方的日本国籍。但事情并不是这样。当然,国籍的因素对她是有点影响的。毕竟来自一个发达国家。况且,她还是日语系的学生。但她并没有那么坏。在她看来,就像中国人里有好有坏,日本人也一样。而且,对方也不过是个普通的日本人。为老板打工,拿一万块一个月的薪水,这点钱拿到日本去,简直少得可怜。除了中文说得比较蹩脚外,和其他中国男人没什么两样。 那个日本人其实是她的学生。大三的时候,她找了份家教的兼职,教那个日本人中文。一个星期两次。刚开始的时候,她纯粹是为了打份工,赚点零花钱。这些钱可以让她不时给自己买件漂亮衣服。毕竟年纪不小了,总开口向父母要钱,她会觉得不好意思。那个日本人住在莘庄的一栋复式公寓里,是他公司分给他的宿舍。在那套装修还算考究的房子里,他和其他几个日本人一块儿住,有一间朝南的屋子。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的晚上,她乘地铁去给他上两小时的中文课。那间屋子里只有一张书桌和一张双人床,铺着一块有骆驼图案的波斯地毯。他们一般就席地而坐。她给他上国内小学的语文课本,一边用中文交流彼此的日常生活。每个月,她可以拿到一千二百块的学费。这曾让她的同学非常羡慕。 一开始的时候,她对那个日本人并没有什么感觉。那个男人长相一般,身高一般,就是衣着也和中国的年轻人差不多。这几年,上海经济发展得很快。上海街头的流行服装已经和世界同步。来打工的外国人到处都是,已经不能让人刮目相看。那个日本人曾对她说过,上海和东京已相差无几,再过十年,亚洲的经济中心几乎肯定是上海。这些话从那个日本人嘴里说出来,让她产生了一点点自豪感。她并不是很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人。她对那些网上的叫嚣一直不以为然。在她看来,那种明显的嫉妒不仅毫无用处,甚至有点可怜。普通老百姓嘛,哪儿都一样。又何必骂人骂得狗血喷头呢。倒是那个日本人对中国的赞赏另她心生感激,并不由得对他产生一点点好感。 路灯亮起来了。几乎是同时,那一排延续到广场尽头的欧式灯柱开始发光。那种灯嵌在灯柱里,长长的一根,竖着的,开始还很暗,过一会儿就发出明亮的光来,白晃晃地将广场照得遍地生辉。她的影子变得黑漆漆的了,就像只倒扣在地上的小黑锅。她梳弄了一下头发,觉得有点冷。 他已经走了吧,她想。他应该回学校上课了,那个遥远的外地,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有多远呢?她思忖道,可能也不是很远,在地图上,只是小小的一段,比起他到过的地方,这点路程根本不值一提。但她却无法想象。长那么大,最远的地方只去过苏州。那还是高中时的一次秋游,去苏州乐园。坐了一个小时的汽车就到了。那时,她还不认识他。高一吧,他们还刚刚入学。她记得那个乐园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还有蹦极,把两个人捆在一块儿,用绳子系住,先拉到空中,再扔下来。她的几个同学都去玩了。据说很刺激,但她没去。在她看来,那太可怕了。好端端地站在地上多好啊,为什么要把生命交给那根看上去不很结实的绳子呢?看见她的朋友在空中尖叫,她真为她们捏把汗。“玩得就是心跳嘛。”下来后她们趾高气扬地对她说。她对此虽然装出不屑一顾的样子外国人买烟的价格,但心里还有点发痒的。活着到底为什么呢?为了刺激?她一点都不明白。不过,她知道自己永远会是那个站在地上,为别人拿衣服的人。 其实,她对他说,她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坏的意思是:她已经不是***了。在半年前的一个晚上,她和那个日本人睡了,还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那时,他正休学旅行回来,并和她见了一次面。在那个位于福州路的星巴克咖啡屋里,他向她侃侃而谈了那次旅行的经历,还给她看了很多照片。那个下午,一直都是他一个人在说话。她只在一旁静静地听。听那些旅途上的奇闻逸事,听他独自背包访神山的伟大事迹。“最高的卓玛拉山口有五千七百米。到处是雪,而神山就在一旁。山上的积雪晶莹剔透。让我不禁想高声呼喊。”他曾那么说道。他的表情神采飞扬、就像凯旋的英雄,丝毫没有注意她的感受。其实,那一刻,她突然觉得他们已经不可能成为情侣了。虽然在此之前,他们也不过是朋友。她记得在那封拒绝他的E-mail的结尾,她曾这么写道:我们的关系的确有点奇怪。那怎么办呢?就奇怪下去吗?这对你可能无法接受吧,对谁都不好接受吧。写下这句话后,她就哭了。她对着屏幕泪流满面。她终于拒绝了他。但,这难道不是真的无可奈何了吗? 那天后来,他们还去看了场电影,是张艺谋的《英雄》。她记得那部片子并不十分好看,有些地方还让人发笑。但她已经不记得剧情了。看电影的时候,他就坐在她身旁。他看得很仔细,目不转睛,嘴边不时地露出他一贯的冷笑。他在看电影,已经把她忘记了。而她却在看他。她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怀着那种心态和他见面。虽然,以后他们还会见面,但她却不会再那么傻,再幻想着他是她的男朋友了。 一片梧桐树叶子飞下来了。飞到她脚边。她把它捡起来,仔细地看了看它。那不是片好看的叶子,缺了一角,干枯的叶面也有几个破洞。那是在光秃秃地树干上最后停留的几片叶子之一吧。冬天已经来了很久了。它一直挂在那里。最后,还是被风吹了下来。她转动着细细的叶柄,觉得心里的怅然更浓了。 她只和那个日本人做过一次,以后就再没做过。那个日本人倒是挺好的,从来不提这方面的要求。就是有时在约会时想亲亲她,也会征得她的同意。这令她很满意。觉得他像个绅士。她是知道男人的。男人这种东西嘛,和女人不一样,总是想着那件事的,否则他们为什么总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壮呢?在日本人的房间里,放着两只大哑铃。她曾坐在一旁看他运动,他手臂上的肌肉鼓鼓的,很有力的样子。有时,还会转过身向她得意地展示。那些肌肉挂在他身上,在光线里不停地变化。有时,也会令她感到一点兴奋。女人总喜欢有力的男人吧,否则,怎么会有安全感呢?他,那么瘦!看上去甚至有点营养不良。尤其是他从西藏回来那会儿,整个人都似乎在空气里飘着,好像一阵风就能将他吹走。这令她既担心,又不安。这样的人怎么保护一个女人呢?靠什么?浪漫?还是那个日本人值得信赖,有工作,有计划,又强壮,而且从不对她动手动脚?这说明他很爱她。这令她感到愉快,甚至有点幸福的意思。 不过第一次,他依然伤害了她,令她觉得很疼。那个晚上,原本她不准备去的。她都和他说好了,有个朋友要来,她要陪陪他。但事情的转变出乎她的意料。她终于绝望了。男人不会知道女人绝望的心情。那一刻,她变得很无力。他们在电影院门口分手时,她几乎都不想站了。他一点都没有察觉,他何时认真留意过她呀。或许在他那时看来,她不过是他的一个普通的女性朋友。这样的朋友一定很多,让他已经学会对每一个都漠不关心了。在微笑地打过招呼后,他们就分手了。原本,她还想请他吃晚饭,并继续和他聊天。原本,她还想跟他回他的住处。她等了他几年了。他的回归令她满心欢喜。他玩够了吧,他该回家了吧?但显然,她又一次自作多情了。 她出现在那个日本人面前时,对方有点吃惊。因为她已经哭红了双眼。她不知道那个晚上流了多少泪。望着他的背影,他消失在公共汽车门前的侧面。她的泪不停地流,好像没有流干的时候。她不是个喜欢哭的女孩。好像从高中开始,她还没哭过一次,无论是考试考得多么糟糕,或是在朋友那里受了委屈。看到他和他当时的女朋友在一起亲昵,她都没有哭过。她想她还算是个比较坚强的女孩子吧。但那天晚上,积攒的泪水却像春天的雨一样下个不停。让她自己都感到奇怪。等她来到那个日本人宿舍门口时,她已经再也流不出泪了。他很惊慌地问她怎么了,用她教给他的那几句生硬的中文。她呢,却和他说日语。她学了四年日语,但却无法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感情。于是在无可奈何中,她向他扑了过去,扑倒在他怀里,一边亲吻他。他也很激动。于是,几乎水到渠成般地***了。在那张原本显得有点空落的双人床上。在他初次进入她身体时,她最后一次流下了泪,只有一点点。她不知道是因为疼呢,还是因为难过。她终于失去了***之身。二十二岁,给了那个还不怎么会说中国话的日本男人。 怎么想着想着想到这里了呢?她摇摇头。回过神时,她发现那片叶子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她揉碎了。她有点不好意思,就用一张餐巾纸把它包起来,准备扔进一旁的垃圾箱。起身的时候,她看见了放在一旁的香烟。“对了,不是准备试一试香烟的吗?”她想,一边就把那根已经***的香烟夹进手指。 她端详了一会儿,下定了决心。但真准备这么做时,她发现好像缺了点什么。 “对了,还要火。没火怎么点呢?”想到这里时,她又懊恼起来。为什么买烟时不顺便把打火机一起买了呢?她抬头望了望不远处的那家小便利店。那里亮着白色的灯光。一个穿大衣的中年妇女正提着塑料袋推开门,而那个令她不快的、穿着制服的老头儿正在收银机前低头敲打。 算了吧。她终于泄气了。回去还要继续写她的毕业论文。晚上,还要接那个日本人,她男朋友的电话。发什么神经呢?她想着便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了几步,最后犹豫了一下,便把那包十二块八的香烟连同被裹起来的枯叶一同扔进垃圾筒。 “那个女孩好像很奇怪哦。”一个清洁工对他的同伴说,“她是个学生吗?”说着他们就翻起了垃圾箱,把那包被丢弃的香烟拣出来。 “运气不坏呢,是包‘好日子’。”说着,两个幸运的清洁工就彼此为对方点起了烟,一边望着那个步履缓慢的女孩的背影,心满意足地抽了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