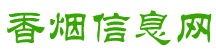|
上海一条很普通的弄堂。 弄堂口的过街楼正中央的石碑上刻写着“福禄里”三个字。沿着这条路向北走去,天宝里、福庆坊、南阳里一字排开。每一条弄堂的名字里都有一段故事。究竟是什么故事呢,没有文字的记载,久而久之人们早就忘记了。居住在石库门里的人常说的是某某是住在某某里或者某某坊几号的。路上遇见的时候会问,侬到福庆坊去啊?勿对,我去南阳里找李家嫂嫂搓麻将。那些挂在弄堂口铁皮牌子标明的某弄数字号码只是在写信的时候,户口登记的时候才会被记起。 一般的弄堂里左边从1号到11号,右边是从2号到12号。这样有规则的排列就像上海人细腻、严谨细致、有规有矩一样井井有条。福禄里弄堂口是一条通行有轨电车的马路。有轨电车开到弄堂门口时,因为路旁一块荒地阻挡了去路,马路在这里拐了一个弯,成为一个丁字路口。 头顶着电线,一根小辫子连着车厢顶端,脚踩着两根铁轨。有轨电车“叮叮当当”的响声在慢悠悠地告诉你这座城市的苏醒了,睡眠了。夏天的时候,在路边上街沿乘凉的孩子们会趁大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捡起一块小石子飞快地跑过去,把小石子放到有轨电车的路轨里。有轨电车晃悠悠开过来,义无反顾地碾压小石子。咔嚓、咔嚓,发出沉闷的响声时,小朋友们会高兴地拍手。要是被大人们发现了,轻的是一顿训斥,重则就是一顿打。“小赤佬,要是电车翻了,侬去吃官司啊!”。福禄里的大人们都知道,住在5号里的李长根的儿子小黑皮经常带头干这样的事情,爷娘也勿管的。 上午,住在5号里楼下西厢房的宝哥哥爷爷走出大门。他看见身穿着绿色军装的一群学生来到5号里的门口。一个拎着一捅还冒着热气的浆糊桶,一个举着扫把在桶里沾上浆糊后快速地朝墙上的大字报上刷去,均匀、平缓。刷浆糊的脚步从左向右移动着,跟随其后的人把报纸大小的白纸覆盖在贴在5号里门口墙壁的大字报上,抚平、粘紧,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一直站在刷浆糊的学生身后的那个戴着深度近视眼的学生左手提着一个小油漆桶,右手握着一支排笔。他稍稍弯下腰香烟一手,从第一张白纸的位置开始,在湿漉漉的纸上挥舞起手中的排笔。墨汁融化在纸上,浆糊的水分尽情地吸允着墨香,交织着、融合着。瞬间一行字布满了—— “刘阿贵破··坏上山下乡罪··责··难逃!”落款写的是“卫东中学红··卫··兵团”。写完了,人就走了。很快,就几分钟的时间。提着浆糊桶的、拿着刷把拎着装有墨汁漆桶的、怀抱一卷大白纸的,齐刷刷地开步走了。他们好像是一群机械人,做完了,好了,走了,急匆匆地赶向下一堵墙去,继续着如此一般的操练。 宝哥哥的爷爷没有看这些人远去的背影。从1966年的夏天开始时是惊讶,然后是好奇,现在已经是习以为常了。这回他看得很仔细。这手字写得不错!宝哥哥爷爷一直在仔细观赏着这一行字。隶书字体,写得不错。看来这位书写者是拜过师的,一笔一划都有着自己的韵味。你看这每一个字的 “蚕头燕尾”、“一波三折”掌握得很得当啊。煞风景的是怎么把阿字和贵字都倒写了。嗯,现在兴这样写法。上至刘··少奇、邓··小平,中间的有上海的陈··丕显、曹··狄秋,下至底层的各种坏人,这些人的名字都要倒着写的。没有用红墨汁在名字上打上个叉叉算是幸运的。 宝哥哥爷爷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牡丹牌香烟,用手一弹抽出一支烟点燃后。透过一缕烟雾,再细细看了一下后心想:你要打倒人家,写这个隶书不好。还是魏体好。森严规整,刚劲有力一些。不过,现在的孩子能够写出这样一手好字不多见了。哪像阿拉以前,练毛笔字的萝卜干饭要吃上几十年才像回事情。现在倒好,毛笔勿练了,都用自来水笔写字了。没有一点笔锋了,唉,就是年代不一样了。我看这个写字的后生啊,肯定练过,要是在以前好好教教,讲勿定会成为一个书法家呢。 大标语上一些字墨迹未干,墨汁像一点一滴泪珠流淌下来,宝哥哥爷爷心里暗暗为刘阿贵叫苦:阿贵啊,侬又要倒霉了,弄勿好又要皮肉之苦啦,唉。烦勿着与人家作对吗,最终吃苦头的还是自己。老刘啊,就是缺个心眼。勿对,缺文化,只会做做五金活,勿会看风使舵啊! 5号大门吱呀一声开了,宝哥哥奶奶端着一大盆刚洗完的衣服来弄堂里晾晒衣服。“今朝太阳好,要快点了。” 宝哥哥奶奶看见自家的男人站在一旁发愣,赶紧促他:老头子啊,侬做啥啊,还勿去给儿子寄信啊。侬发啥个呆啊! 哦,宝哥哥爷爷愣了一下,把已经烧到手指的烟屁股一扔,急匆匆地朝弄堂口走去。 白天,弄堂里来来往往的人不多。来去匆匆的人、慢条斯理的人、无所事事的人走到新刷的大标语前都只是看一眼就走了,啥人也没有把它当一回事情。傍晚,下班回家的人走进弄堂,在这条新标语面前放缓了一下脚步,看了一眼便各自朝家里走去。 旧的大字报和标语不断被覆盖,新的大字报和标语不断出现。大字报、大标语从马路上延伸到了弄堂里。除了还能够看见的窗户外,墙壁上早已经被各式各样的白纸、报纸盖住了。花花绿绿、五颜六色。石库门房子的红砖外墙在未被覆盖的墙角下才依稀看的到。 1966年的夏天后,生活里多了一个看大字报、大标语的内容。老人还记得,十年前大··鸣··大··放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大字报。那会儿还没有这样一张报纸大小一个字的大标语。只是啥人也预料勿到啥个辰光会轮到自己的头上。 被指名道姓的刘阿贵住在5号里楼上的东厢房里,大家习惯叫刘家伯伯。宝哥哥爷爷前脚刚走,他提着一个大扫把从5号大门出来。 “又是一条标语?”刘家伯伯抬头看了一眼,哼,又来了!这帮子小赤佬! 刘家伯伯“哼、哼”两声扭头朝弄堂口走去。伊那里开始把整条弄堂扫一遍。这是刘家伯伯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被勒令每天要做的事,天天如此,风雨无阻,没有休息日。 刘家伯伯每天都穿着一件背带裤工作服。冬天的时候,宽大的工作裤套在棉衣外,夏天的时候光着膀子还是这件背带裤工作服。前胸口袋里永远装着的是一包飞马牌的香烟。除了夏天,刘家伯伯头上一直是那顶黑乎乎的鸭舌帽。右耳朵上夹着一支铅笔。鸭舌帽下一道浓眉下两只大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香烟一手,有神,还有一丝丝慈祥。刘家伯伯嘴上的香烟一个接着一个,一缕缕青烟慢慢悠悠地冒着。一根完了,他会从前胸口袋里掏一支香烟,然后把快要烫到手指尖的烟屁股把烟接着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与渗出的口水一直不离开刘家伯伯嘴唇。 这样的标语5号里的人都记得,开始的时候有“打倒坏分子刘阿贵!”,以后又有“打倒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坏分子刘阿贵!”,“刘阿贵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等等,一直没有消停过。反正隔上一段时间就要来一回。对于5号里的人来说,其实不止是刘家伯伯一个人。像住在5号前楼的邮局的吴局长,昨天还是邮局的局长,第二天就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在单位里与刘家伯伯一样,扫地打扫厕所,分发邮件,背麻袋包当运输工。吴局长的老婆被揭发出来是个国民党的“潜··伏··特··务”,还是个“美女蛇”,勾引革命军人(指吴局长)。与刘家伯伯隔窗相望的是我家,我的父亲是“右··派··分··子”,与刘家伯伯一起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阶级敌人了。楼下的小学周老师是“反革命分子家属”、“反动学术权威”,运动开始后不教书了,每天要到学校里的“牛··棚”报到写检查。还有在工厂里跑销售的夏家叔叔是个“贪污腐化分子”;楼下的二房东老爷爷是“资本家”……谁知道还会轮到哪一家又被戴上了新的帽子呢。唉,5号里的坏人一下子多了不少。 门口的大字报换了又换,大标语刷了又刷,厚厚的堆积在墙上。一阵风过后是一阵雨,贴在墙上的纸张散落了,卷起的,残落的,一幅破残败落的模样。 其他门牌号码也差不多,只是5号里的坏人多。住在福禄里的人都把阿拉5号里称之为“牛鬼蛇神之家”。 (责任编辑:admin) |